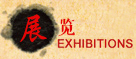刘思源
一

鲁迅的“革命优先论”是有感而发,且有时代的因素,如果把鲁迅的看法看做章太炎的盖棺定论,恐怕会有不少人不同意,乃弟周作人就认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但不管怎么说,章太炎首先是以革命家现身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建立卓著的革命功勋,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慕顾炎武、黄宗羲的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他出身书香门第,少时随外祖父朱有虔读书,曾读《东华录》,愤恨满清之入主中原,埋下了种族革命种子。又因他体弱多病,家人认为他不适于残酷的场屋鏖战以博取功名,遂从此绝意仕进,专心学术。
1890年,章太炎进入杭州著名的书院诂经精舍,受业于大学者俞樾门下,苦读七年,打下作为古文经学家的扎实的学术根基。古文经学重名物训诂,重典章制度,这对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产生了不小影响。他光复汉家旧物的主张,发扬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热情的主张,以及种种带有复古色彩的主张,不少是从他的学术思想生发出来、移植过来的,或者说他用学术来证明服务于他的革命主张,这是他不同于孙、黄等其他革命家的重要特色。
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大师,在学术上是章太炎的死对头,章太炎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新学伪经考>驳议》(未完成)。但国祸日亟,为了救亡图存,章太炎还是暂时搁下他们的学术分歧,与康梁合作,参加《时务报》,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
1902年,上海张园召开中国议会,与会者多为维新派人物,商量着如何勤王保皇。章太炎忽然跳上讲台要求发言,号召大家放弃保皇立场,彻底与满清政权决裂,宣称即日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之后他还写出名文《解辫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道章太炎张园割辫的行动,收到《解辫发》的文章,立予全文揭载,并附了近乎欢呼式的激赞:“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士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一个革命巨子就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开始了他所向披靡的革命宣传鼓动的事业。
三
《苏报》本是上海滩一份无名小报,1903年该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并通过章士钊招揽一批像章太炎、邹容这样的爱国学社师生们撰稿。他们议论风发,昌言革命排满,使得报纸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影响越来越大,读者越来越多,销量激增,俨然成为上海革命派的言论喉舌。
在《苏报》所有的革命言论当中,章太炎的文章当居翘楚,尤其是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这也成为《苏报》案的起因,成为他被捕入狱的原由。《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劈头就说:“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辞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盅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这是骂康有为。接着说“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是骂当今皇帝。接着又说“然则公理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是歌颂革命。在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历史主导权的关键时刻,章太炎挺身而出,对保皇派作了致命一击。他在《苏报》上革命言论及其后发生的《苏报》案,确立了章太炎在革命阵营中头号宣传鼓动家的地位。
对于这些公然造反的言论,岂能坐视不管,清廷早已对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出电令:“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召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著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但章太炎、邹容等《苏报》撰稿人经常活动在租界,租界拥有治外法权,清政府不能进去捕人,只好向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提出控告,由租界当局将章、邹等人抓捕到案。为取得任意处置章、邹等人的权力,清政府要求引渡章、邹,并无耻地向租界当局开出沪宁路权及十万两白银这样诱人的价码。此事为报章所披露,群情汹汹,清政府只得打消引渡的念头,而作为原告与章、邹等人打起了官司。
在《苏报》案的审理中,章太炎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自信从容和凛然正气。他这样回答攻击他的记者:“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祀天,光复旧物,而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性,秒忽相衡,斥鷃井蛙,安足知鲲鹏之志哉!……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在法庭上,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章太炎表现得义正辞严,意气轩昂,而控方则处处显得狼狈可笑,猥琐卑鄙。一时间,《苏报》案成为上海各报争相报道的焦点,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革命者的气节风范,得到广泛传颂,革命排满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四

1906年7月,因《苏报》案被判刑三年的章太炎终于出狱。同盟会早已派人迎候在那里,他们要把章太炎接到同盟会总部所在地东京,请他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发挥其在革命宣传鼓动上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作用。此时的东京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大批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留日学生汇聚到这里,革命团体先后在这里成立,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先后来到这里,《民报》、《浙江潮》、《汉声》、《江苏》、《河南》等革命刊物在此创办,因此,章太炎的到来,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主持同盟会召开的欢迎会,欢迎会那天下着大雨,但仍然有两千多名青年留日学生聚集到清国留学生会馆锦辉馆,他们要一睹这位传奇英雄的的风采,一聆他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高论。
章太炎披着长发,身体因三年牢狱之厄而略显浮肿,慢慢地用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发表他洋洋万言的演说。这演说简直就是一篇“神经病论”。他说:“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的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恼,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 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这真是一番千古名论,对于长期受君主专制思想束缚的人,对于想冲决网罗,打破枷锁的人,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解放。
章太炎素有“疯癫”之目,这番高论算是对世人的回答,也是对世人的挑战。据鲁迅回忆,章太炎好发议论,任意褒贬人物,毫无顾忌,常常令人难堪。无奈之中,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假如章太炎说了对他们不利的话,他们就在报纸上发表时加上标题曰“章疯大发其疯”,疯子说的疯话,自然做不得数。假如章太炎不小心说了对他们有利的话,发表的时候,标题就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讲学之暇与弟子闲聊时,也时有高论。比如他说给小偷定罪不以所偷财物多少为定,而以所偷财物占失主财物比例科罪。假如偷的是穷人,一个铜板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也要科以重罪。假如所偷为富人,虽则成千上万,但占失主财产比例甚小,其罪甚轻。
五
从1906年东渡,到1912年归国,章太炎在东京差不多呆了六年。这一时期,是他革命生涯的高峰期,也是他讲学的高峰期,还是他学术上创获最多的时期。1908年,章太炎开始了他首次讲学,先后入门听讲受业的有黄侃、钱玄同、吴承仕、汪东、朱希祖、朱宗莱、钱均甫、龚未生、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此次讲学所得人才之多,成就之大,方面之广,对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影响之深远,在古今学术史罕见其匹。
周作人回忆说:“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天,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章太炎是主张光复汉家旧物,发扬国粹的,因此在章门复古的空气与革命的空气一样浓厚。字要求古字,礼要复古礼,一切名物制度也是愈古愈好。到1912年,钱玄同还写出《深衣冠服考》,并亲自制作所谓深衣穿上,进行复古礼的实验,也就不足为奇了。
章太炎长于议论,而拙于实行,革命成功后,他虽然仍然致力于政治,但其主张与孙、黄派每多扞格不合,其郁郁不得志是必然的。坚决反袁是他后期革命生涯的闪光之点。1913年,章太炎孤身北上,对于急欲称帝的袁世凯来说,无异是自投罗网,于是就有了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之一幕。袁世凯希望章太炎如筹安会诸君子,赞助其称帝,即使不愿赞助,也不要昌言反对。章太炎的大骂不止,令袁世凯极为恼怒,他把章太炎软禁起来,使尽威迫利诱的手段,仍然不能使他屈服,并遭到他多次绝食反抗,章太炎还大书“速死”二字以示决心。
说到底,章太炎是个学问家。革命前他是学问家,革命中他是学问家,革命后他仍然是学问家。只是他的学问过于奥博,过于专门,一般人难以触其藩篱,这自然也是本文力所不及的,所以只能多介绍学问之外的事,学问还是照抄弟子们的评价为好。许寿裳说:“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钱玄同的挽联对于其人其学的评价也很扼要。联曰:“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续而革命,蛮夷狄戎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士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六
章太炎的书名很大,求字的人极多。他的字是一种典型的学者之字,功力深厚,无论篆书、行书、楷书,都具有一种笔势雄强的面目。据说,章太炎自己并不十分珍惜他的字,往往一幅写成,略不满意,即纳之字纸篓。这给了侍役一个赚钱的机会,竟串通一家装裱店,专窃这种字,印上章太炎的图章,装裱出卖。章太炎初不在意,发觉后倒也想了一个防弊的方法:把图章从侍役手中收回,作废的写件一律撕掉。岂知撕碎的字照样可以裱起来,而图章则待到章太炎把图章交侍役清洗时再盖不迟,因此,该侍役窃字的生意并未中断。(据许寿裳《章炳麟传》)
另据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章太炎东京弟子之一汪东想以章太炎的名义办一种月刊《华国月刊》,所需经费全由用章太炎名义卖字所得抵充,润格订为对联每付十元起价。汪东有一样本事,就是模仿他章老师的字几可乱真,因此所有写件皆由汪东代笔,再由章太炎书下款钤印,然后交各名店发卖。卖字事业居然十分不错,润笔所积有十万元之多。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章太炎手迹79件,有书札、扇面、对联、匾额等。此次选刊XX件,大体可以反映章太炎各种书体的面貌。这些手迹都是章太炎写给他东京的大弟子们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的,所以决不会有上述两则轶事所说的那种情况,皆为章太炎的精意之作。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早年为章太炎写刻《小学答问》,晚年则为老师写刻《新出三体石经石注考》,为师门任事独多,行迹较密,情谊复笃,因此所得章太炎手迹亦多。鲁博所藏79件手迹中,有近70件是写给他的。钱玄同把章太炎写给他的59通手札,一一用红笔标注时间地点,并按时序粘贴成两册,差不多编成一部“先师章太炎先生手札”了。手札内容大多为师弟之间问学切磋之事,动辄娓娓数千言,仿佛一篇
一篇的讲义,那么把这部手札,视为《小学答问》的外篇,似无不可。
行草书体是章太炎日常所用,所遗手迹最多,一般书札皆是,如他写给钱玄同的手札。章太炎的行草书(包括楷书),时显倔拙之气,每多篆隶之味,与流媚的帖派之书大异其趣,他的篆书则一以《说文》为正,面貌较之其他书体要圆润得多了。历史上书以人名、书以人贵的事常有。章太炎是革命元勋、国学大师,书法别具一种倔拙雄强的风貌,所遗手迹为世人所珍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假如世人仅知珍其字,如那窃字的侍役一般,而不知珍其文,珍其学,珍其人,则珍其所不当珍,所失多矣。“书者,心画也。”书如其人,世人摩挲鉴赏这些手迹,进而好其文,好其学,好其人,景行先贤,想见其为人,则其人其书就可以同其不朽了。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