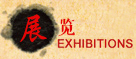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五四”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一个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鲁迅的五四”毫无疑问是指作为个体的鲁迅历经这样的历史时刻,以怎样别样的方式介入,又如何构建了无法取代的独特的新文化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向“和会”提出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侵夺的山东权益等要求,结果遭到拒绝,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5月1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向国内发回电报,告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梁启超遂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徐世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约,由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送徐世昌,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偷偷将消息泄露给林长民。林马上到会报告,汪大燮非常焦急,叶景莘说:“‘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与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他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元培的住处。当晚九点左右,蔡元培召集北大学生代表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康白情“五大领袖”到他的住处,告知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即将签字的消息。
5月2日,蔡元培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电令陆征祥等专使签字于和约,结果又为赴法勤工俭学事业而奔走的李石曾所侦悉,遂由巴黎密电蔡元培。蔡阅电后,一边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和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三人联名致电陆征祥,劝其切勿签字;一边通知北大学生代表,并紧急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商讨救济办法。与会者愤于北洋军阀政府在对日交涉上的卖国行径,以及对北大的敌视,主张对学生运动不加拦阻。
当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刘庆平同学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刘仁静同学则拿出一把菜刀来欲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会上决议:一、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蔡元培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北大学生费了一夜功夫把打电报省下来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元钱拿出来买了竹布,做了三千多面旗子。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翌日晨,又预备了一个英文备忘录,准备送给各国使馆。
5月4日上午9时许,北大和高师、工专等13所大专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继续开会,商议当日天安门大会的议程和会后游行示威路线,同时通知各校准备旗帜、标语。10点钟,罗家伦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站在一张长桌旁当即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全部汇集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军警欲用武力驱散学生。学生代表纷纷发表演说,散发罗家伦起草的宣言传单,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旋即开始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抗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起初,学生们并无意冲击政府机构,而是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求美国使馆帮助。因为是礼拜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去西山踏青了,但工作人员接受了所递送的学生陈词书的英文备忘录。而英法意使馆却拒绝接受。学生出而要求经过东交民巷,结果遭到警察拒绝。气盛性直、不经阅历的学生们深感在自己的国土上行动都不自由,群情愈加激奋,临时动议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找卖国贼以泄愤。当时,傅斯年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然而,极力劝阻已经不起作用。守卫曹宅的军警第一次遭遇这样情况,面对学生队伍,没有接到命令,不知如何是好。学生们便破窗而入,开始打砸家中什物。在客厅中发现了章宗祥后,立刻拳脚相加。纷乱之间,曹宅火起,一直烧到晚上八点。后巡警缉拿学生32人。
北大学生齐集第三院法科大礼堂开紧急大会,蔡元培邀同法律专家王宠惠与会,研讨营救被捕同学的法律手续。天亮后,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学界纷起响应声援。
5月6日,蔡元培等五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注销《校长布告》,不仅不接受教育部关于开除为首滋事的命令,而且表示“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全国各界来电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北京政府为避免酿成激变,提出复课条件,蔡元培等当即承诺后,学生释放,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5月8日,蔡元培即向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递送辞呈,9日离京。
5月18日罗家伦在“北京学生总罢课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一名词,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再造中国的元素”,其精神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激起全国更大的愤慨。上海、武汉、南京、天津、杭州、九江等地工人举行首次政治罢工,各重要城市商人先后罢市。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在我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变时期发生的,它是标志着我国新民主革命开端的伟大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转捩点。五四运动之后半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正式出现,到1920年初才流行开来。实际上,1915年《青年杂志》和《科学》杂志的创刊即为新文化运动的上限,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平息为下限。这是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的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并发展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提倡白话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首先在《新青年》倡导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成为文学正宗,在与复古派的激烈论争中逐步得到推广,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采用。从“五四”到“新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并共享了一种横向扩张的运动机制。五四爱国运动实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同时又扩大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鲁迅在干什么呢?
校长蔡元培未曾离开过红楼,心系学生们的安危,不食不眠;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指挥“学联”“教职联”有组织的工作;陈独秀则为《每周评论》奋笔撰稿,把群众对卖国贼的痛恨情绪引向北洋军阀政府;而作为北大国文系兼职讲师的鲁迅却是奔丧去了,因为不是正式教职,又是星期日,他并没有在现场。查看当天日记,和所有日记一样,只有寥寥几字,“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不仅如此,从5月4日直到6月,鲁迅的日记中没有任何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词,生活与心情都是平淡无奇。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在给自己的学生写的一封信里,我们才看到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明确评价——“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守旧派将其视为一切乱象的根源,将学生称为祸萌,是冤枉的;而革新者将学生誉为志士,赞扬甚至,又太过份了,致使“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
鲁迅当然是同情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的,六年后,也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年,在杂文《忽然想到七》中,提到五四学运的场景,他写道:“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
他将“五四运动的策动”看做是“北京学界”的“光荣”,以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扬”,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的开端。
鲁迅没有选择武装革命,做流血的革命志士,也放弃了拯救肉体痛苦的医学,更不会去领导学运,参与激进的政治斗争,那么,传播和建设新文化便应该是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主战线。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鲁迅是“思想界的盟主”,“思想界的权威者”,这些言犹在耳的历史评价在最初的语境下诞生时,都是合情合理的,却远非“真的猛士”更接近鲁迅本身。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介入的方式仍是一贯的被动低调,他并没有也不需要如历史评价那样“权威”地去表现自己。
他远离时代的喧嚣和躁动,却也遵奉五四文学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统一步调,默默地以别具一格的白话著作显示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那么,在鲁迅眼中,这一次“颇有些成功”的“革新运动”是如何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容与态势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
新文化倡导者又做出了哪些惊人之举,不凡业绩?
中国长期以来用“难懂的古文”讲着“陈旧的古意思”,新文化的前驱者提倡“文学革命”,志在尝试让哑然沉默的中国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此改变“无声的中国”,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艰难到类似于宗教上的奇迹。
于是首先要来一个“文字上的革新”——提倡白话文,实际就是倡导民众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而去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而是学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这样才能使文字成为“大家所公有”。
然而,如此简单的道理,明确的意图,被以“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却使很多人一听到便如遭逢洪水猛兽般害怕,各方面剧烈的攻击反对之声纷纷而起,新旧势力很是恶斗了一场,但后来还是渐渐风行起来了。貌似提倡白话者势如破竹,尤其打了几处漂亮仗,如钱玄同刘半农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上演的双簧戏,实际情况却是,有比这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那就是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来也只是关于文字革新的个人设想之一,在知识界来看,应该是很平常的争鸣探讨,然而,在那些不喜欢听改革之声的保守派看来,可是天大的事,比用白话取代文言更不能容忍,比较之下,提倡白话反倒显得平和了,于是便放过文学革命,全力以赴来围剿这一观点,攻击白话文的敌人反而随之减少了,竟仿佛没有阻碍似的流行起来。
待到倡导白话文见了成效,势不可遏,形形色色的人物又开始上演各种把戏——冷笑家收起嘲讽,开始拍手赞成;投机者“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两面派则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并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调和派却说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希图多留几天僵尸。
这样看来,只是“文学革新”,是很不够的,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又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与白话文的普及同时进行的是新文学家们通过现代传媒营造的新文坛,北大学子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新潮》杂志,出现了一批“为人生”的作家群,他们以文学为“有所为”,把作品视为“改革社会的器械”。而“为艺术而艺术派”也以艺术的自主性向‘文以载道’说进攻;新文学比照西洋文学,将中国传统视为酒余茶后消闲品的小说提高到主流地位,于是新的智识者取代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及至后来的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成为故事主角,略带些残余的英雄和才子气,算是较为清新地登场了。从此,小说家侵入新文坛,白话小说在不断的战斗中生存。“含着挣扎和战斗”的散文小品,却是取得了空前成功,胜于其他所有文学样式,而当此时“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
至于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鲁迅却直陈只是一小部分,特别是当《新青年》四面受敌之时。即使留下了些许文字,也都是应时浅薄的,应该置之不顾,一任消灭。而在后世史学家看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实绩的作家,鲁迅却是通过创作做出了独特的诠释。《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成功的白话小说,中国文学由此真正跨入现代。他借狂人之口忧愤深广地说出中国历史全是“吃人”的真相,完全颠覆了传统价值。此后八年,他连续作成25篇,几乎一篇一个样式,捧出一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在内容形式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令陈独秀主编“五体投地的佩服”。创作《狂人日记》的同时,他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配合“反抗传统,破坏偶像”的编辑方针,发表一系列热忱健朗,深沉激越,现实关怀的文明批评,使杂文成一独立文体,如匕首投枪,不断刺向无物之阵。
在鲁迅看来,作为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成功是表面化的,社会固然太守旧,而主张革新的虽蓬蓬勃勃,却是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队伍纷乱芜杂,反反复复,“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穿着“拟态的制服”,最终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这样的四周吹着的空气只能说是寒冽的热风。
后来摧折新文化的又很不少。本国人的批评不冷不热,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最初是肯定其意义的,攻击者则以为革新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在鲁迅看来,这些观点提出者自身都不是改革者,怎能站得住脚。
1920年,鲁迅便预料到,“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然而,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他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不是官吏所希望的现状,也不是新学家所鼓吹的新式,只有一塌胡涂。
此是危言耸听吗?自《新潮》群中的健将,远赴欧美留学,支持着《新青年》的人们,风流云散,新文化战士或“高升”,或“退隐”,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招安”之感。“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又下不到十年,五四已令人殊有隔世之感。
且看五四之后出现的诸多流弊——一些投机家借它来牟取名利,出版界上出现了“文丐”和“文氓”,“明版小说”的价钱飞涨;文化界发生了迎合西式思维的新习气——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恰如求签问卜”,暴露出自己缺少自信和心存“狐疑”。外国人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中国便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北京大学整饬校风,学生公议以袍子马褂作为制服,这种“恢复古制”的做法,“实在有些稀奇”;有的作家大肆滥用输入的洋货——省略号,以故弄玄虚来代替艰苦的创作;扶乩等封建迷信仍然猖獗;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但还未摆脱“被养”的地位;为人生的文学衰歇了;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派”不但丧失了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沦为“帮闲文学”;“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刘半农用“玩笑”的方式来“嘲笑欧化式的白话”,从学生试卷中“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而“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学运胜利后的学子们也并不就如自己所呼吁得那般“新道德”,当之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在学校里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实在并没有什么区分。
那么,鲁迅理想中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场怎样的革新呢?实际上,他并不是如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擅长破坏旧文化,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散在于杂文、书信中,甚至是五四落潮后的许多文章片段,当然,其中的很多看法并不是当时的弄潮儿们所喜欢听的。
他首先明确,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决非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成长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对立中,因而对于旧文化是有所承传和择取的。尝试是可敬的,改革是必须推行到底的,爱国的基础是学问,“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要想强国,只有熬苦求学。
提倡者自身思想要彻底,要言行一致,不畏艰难,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要有责任感,对于新生事物的缺点要有“有情的讽刺”,而不是“无情的冷嘲”。要清醒的意识到,那些在外国早已是很普遍的道理,一入中国而为新思潮,即被视为洪水猛兽般吓人,在过激的亢奋排斥下,是会发生流弊的,不要看成是新思潮本身的问题。
文化建设者要明确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改革是必须要进行到底的,否则难以生存,何谈发展。
在策略上,手法不妨激烈一点。因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苟有阻碍生存温饱发展的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行动上,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这是必须首先要做出的选择。青年们不要再说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古代的话,这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外国翻译中国书,也并不就代表那书一定是好的,外国人难道就不会别有用意吗?至于“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种观点貌似有理,然而,连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你能指望他肯剪去辫子吗?
青年们还是放弃犹疑态度,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大胆地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用真的声音,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这样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不要以为中国只是做文章难,实际上等于并没有文字。即便是教育普及,文字公有,白话取代文言,识字者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更少。这种状况与古代文字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并无二致,和大多数是无关的。这十分之二足以代表中国人吗?大多数人是沉默的,这难道不等于中国根本没有文字吗?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已经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
因此,坚守个人与灵明为基础的“立人”理想,捍卫个人与精神的价值,才是新的文化建设的基础。革新者应该永不放弃自我的独立性,永不回避挑战本身,对文化周遭要时时做出新的回应,履行对新的文化建设的有力支持。要活在当下,不做刹那幻想,不寄希望于任何究竟——至于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应“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由上观之,所谓“鲁迅的五四”就是可宝贵的鲁迅的新文化传统,也许代表不了整个五四新文化传统,但却是一份独特丰厚的文化遗产。鲁迅虽然对五四事件没有什么即时反应,却更多时过境迁后至今恩泽后世的深刻思考。他是“革新的破坏者”(魏建功语),是持有一种自主质疑式的革命性思维的坚定的革新者,开创了一种清醒独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传统。
他首先反思质疑“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警惕不得不进入的所谓新文化的思维模式当中去。文字是危险的,清醒的改革者不能受语言的驱使,执着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实际上,它的诞生就出自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后来又将其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鲁迅的五四”就是独立思考的自由,为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战的自由,对既定秩序说“不”的自由,发现的自由,质疑的自由,独立发现事物的自由。他关注个体的改变,全面深入地向心灵挖掘,抵抗一切方法、制度、惯例,警惕被它们塑造,从而沦为奴隶。在陈独秀眼中,鲁迅就不附和《新青年》,而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是特别有价值的。钱玄同将鲁迅从元气淋漓的孤独中,自由的本然状态中,拉回现实,要他那样去思考,那样去反应。而“听将令”的鲁迅,亦时时保持从新文化的环境中抽身的姿态,不做新文化机制的奴隶,不做受制于影响、指引、驱使等任何形式的奴隶。他与新文化主流保持步调一致,并以理性态度在一致中质疑;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他“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他的行动是自由催生的,而不是观念催生的;他觉察到已知事物的冲突,不打算深陷其中;他能够看清自己背负的是什么样的重负,非常深刻真诚地探索自己的内心,力争不受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影响,不被承受了几百年的传统与模式催眠。他也并不打算与读者一起分享什么来自另一世界的现成答案,更不要引导大家走一条康庄大道,他是要将自己的探索发现,以一颗“白心”呈现出来,与大众一起感知当下,探讨未知,这个过程是摒弃给予与接受的模式的,是不知道什么是追随者与领导者、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是由自己直接去发现,这就使他的笔下诞生了摧毁一切虚假的宽广的美。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