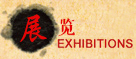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19年的整个辛亥革命历程,贯穿了鲁迅从青少年到而立之年的葱茏岁月,是他个人成长史上青春热血的不朽记忆。“鲁迅的辛亥”所要思考的,一是鲁迅在现实的辛亥革命中做了什么?辛亥革命对他有什么重要意义?一是在鲁迅眼中,辛亥年到底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最重要的,鲁迅至死都是一个战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辛亥“老兵”。
鲁迅的辛亥经历
鲁迅1902年东渡日本,第二年便留下了断发明志的照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豪气丝毫不亚于鉴湖女侠秋瑾的“英雄也有雌!”
他参加了浙江同乡会,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等慷慨激昂的文字。特别是弃医从文后,他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选择的多是东欧弱小受压迫民族的作品,旨在激发同胞反抗强权争取解放的意志。
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组织,包括停留在许寿裳记忆中确定加入了的光复会。对于这个1903年酝酿于日本,1904年10月正式成立于上海,由包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浙江人领导的革命组织,鲁迅自己也只说是接近,更不用说加入同盟会了,尽管他与会员们经常有往来。
不是没有人动员鲁迅,他甚至曾经被命令去执行一项暗杀计划。鲁迅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可以去,也可能会死,然而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处置。革命者见他尚未行动,便先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他去了。
曾经还有一次,鲁迅目睹一位革命领导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聊天,彼时正有下级遵照命令在目标处丢炸弹。震耳的响声传来,鲁迅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杀与被杀者身首异处的惨死图景,他为此坐卧不安。但见那位革命领导却安之若素,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后来鲁迅承认,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自己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就在身边革起命来,或者熟识的人去革命,自己就没有那么高兴听了。
不但如此,作为官派留学生,鲁迅还被自费留学的秋瑾宣判过“死刑”。事情是这样的,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翌日,留学生们共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之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秋瑾主张集体回国,以示抗议;而鲁迅、许寿裳等人,却极力反对。会上,秋瑾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喝一声:“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对鲁迅来说,壮怀激烈的革命情怀是最初阅读时引发的一种起兴,拜伦助希腊独立的肖像,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爱国诗歌,章太炎所向披靡的狱中诗都令其心神俱旺。至少在1905年,鲁迅还没有体味到“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那个时候,清末很大一部分青年被革命浪潮所裹挟,鲁迅便是这特别感应于反抗的青年中的一员,然而,他不同于渴望光复的“种族革命”者——将大号改为“扑满”“打清”,恨的只是辫子,马褂和袍子,希望峨冠博带,“重见汉官威仪”;也不同于复仇主义者——专意搜集明末遗民记录满人残暴的禁书,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促人猛醒,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更不同于极易被捧杀的英雄主义者——歃血为盟,江湖义气,孜孜追求于永生不休的传奇。
鲁迅很少为激进的民族情感所鼓荡。实际上,他一直不满于革命党人狂热的革命浪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暗杀幻梦,赖以成事的队伍又往往意气,侠义,草莽,散漫,诸此种种因素复杂地混搅在一起,形成一种不乏野蛮的所谓“气”,因之鲁迅终究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没有加入光复会也是那个革命圈子里的一分子,即便加入了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保持内心的自由。这从一开始没有执行暗杀计划,到之后作品中的时时反讽,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质疑式思维是一直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得到的。
弃医从文的鲁迅曾经非常有自知之明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谈到这一点:“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意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这样的性情决定了鲁迅将会走在一条孤独漫长的文化启蒙之路上,他注重绍介翻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他用文字记录时代,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撕碎伪饰文明的假面,输入优秀的异域精神食粮,以饲养内心荒芜的民众,而不是直接流血、大叫宣战杀贼的暴力革命。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且对这种“云集”的“应者”,也是时刻要分析分析的。所谓“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正如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鲁迅眼中的“乌托邦”。
辛亥革命发生时,鲁迅已回国两年,并在浙江绍兴府中学堂教书,后任兼学。1911年11月4日,国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宣告光复。绍兴市民召开了一个庆祝杭州光复的大会,公推鲁迅为大会主席。鲁迅发表演讲,提出当务之急是集合学生组成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宣传革命的意义,鼓动民众热情。鲁迅后来每谈及此事,“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
11月8日晚上,鲁迅和学校师生及市民到绍兴西门外迎接光复会会员王金发率领的革命军,一直到第二天黄昏,终于在绍兴偏门外接到。三天后,王金发改组政府,自任都督,并委任鲁迅担任浙江山会师范学堂监督,聘请范爱农担任学堂监学。王金发上任后,采取措施安定民心,他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仓赈,减除苛税,严禁鸦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筹饷扩军,准备北伐。然而,很快就深陷旧势力的捧场和包围之中,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开始任用同乡亲信,大发横财。军政分府首脑是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而治安科长是曾参与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衙门刑名师爷章介眉,本来他已经以“平毁秋墓”的罪名被军政府逮捕,后来却以“毁家纾难”的名义捐献一笔财产,被王金发释放了。
原绍兴府学堂的几位学生于1912年1月3日创刊《越铎日报》,对军政分府施行舆论监督,请鲁迅等为发起人。鲁迅以“黄棘”的化名写了发刊词,指出彻底推翻专制的任重道远,呼吁“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还刊登了很多批评时弊的文章。
这就是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实际参与——演讲、宣传、游行、监督、办报,写批评文章。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鲁迅至南京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部员,从此做了14年的国家公务员,成为国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建者。
1912年,国民政府将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此后,鲁迅的日记中1912、1913、1915、1926年的双十节均明确记录参与观国庆纪念活动。特别是1926年在厦门过双十节,看到厦大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有很多演说、运动、放鞭炮,商民都自动的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这令鲁迅“欢喜非常”,兴奋地给许广平写信诉说这景象。
需要一提的细节是,1913年的双十节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鲁迅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封信,为的是得到特别纪念的邮局印。1916年的双十节,他并去大荔会馆访章介眉,未遇。
虽然鲁迅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革命工作,只是“高兴得很”,自己也志不在武装暴动,但他是赞成革命,并景仰真正的革命家的。徐锡麟、秋瑾就义后,他参加了浙江同乡会举办的追悼会。特别是他后来高度评价孙中山为“创造民国的战士”“第一人”,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都是革命。”“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为了民众心智的健康养成,鲁迅没有选择匆匆赴死,洒一腔热血,而是艰难地活下去。当“城头变幻大王旗”,“震骇一时的牺牲”尤显得“无谓”。他默默隐随在革命先驱者的影子里,记录下沸腾鲜血瞬间冷凝后无尽的苍凉。他独看到,炒食革命党人心肝的不仅是当权者,更有默不作声的民众。他独感受到,悲壮淋漓的诗文与英雄式的名号一样,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真正的革命没有什么大关系。他独质问,就算是存在复仇,谁来做公平的裁判者?难道是自己吗?他独领悟到,“宽恕是美德”,像是没有报复勇气的怯汉发明的格言,更像是卑怯的坏人创造出来骗以宽恕的美名。
在鲁迅心中,比暴力流血更紧要更艰难更伟大更坚实的工作是“改革自己的坏根性”;袭击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令其动摇;攻打中国国民历久养成的目光短浅,“卑怯”“贪婪”的最大病根——尽管这样的改革真叫作“无从措手”,非常之难——然则,不改革“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如何改革?那便是引起群众公愤之余,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勇气;而且还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
事实证明,鲁迅是始终不渝地奋战在这条文化战线上的——怎样点燃民众心中的热情之火,理性之灯,如何照亮他们内心晦暗的角落——鲁迅辛亥葱茏岁月中树立的高远理想,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在为之殚精竭虑。他不是如暗杀式的革命者那样,心中预设了云集的应者,高估鲜血的震撼力量。而是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以勇猛和毅力正视黑暗面,研究解剖文化习惯,于存于废,慎选施行,决不浮游于表面,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停留于书斋中,高谈阔论,大叫未来的光明,欺骗怠慢自己和听众。
这样的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实际上与辛亥革命志士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实现民主,改变专制和奴役现状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他没有选择血的方式,而是选择了言说和输入精神食粮,这种对辛亥革命目标的独异呼应,贯穿一代。革命先觉者的鲜血当然也没有白流,至少换来了众声喧哗的舆论时代,才使得鲁迅这样的思想者成为时代的骄子。
鲁迅的辛亥书写
对辛亥革命的亲历和反思,成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宝贵的精神资源,而文学书写贯穿始终,从处女作文言小说《怀旧》到未完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辛亥成为鲁迅笔墨一生的重要时空坐标。小说中有描写,散文中有回忆,杂文中有批评,日记中有记录,演讲中有评说,他并建议写一部民国建国史。
鲁迅小说中的辛亥书写多采用素淡的笔调,人物线条简单传神,白描下的庸众形态各异,却有着一样麻木滞重的眼神。故事情节均围绕着辛亥革命如何在民间传播而展开。舆论场所包括芜市私塾、华老栓的茶馆、公务员的寓所、临河土场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等。革命党人、提倡改革的知识分子、乃至流氓无产者往往是被当作谈助的话柄,消遣的材料,最终结局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庸众所吞噬。
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革命以“长毛且至”这一消息在小镇“芜市”迅速传播,结果却是一场虚惊。以革命为造反,发誓与之不共戴天的塾师“秃先生”和乡绅金耀宗,被这一消息吓得惶恐失态,千方百计以求自保,但不久即相告平安,仆佣也仍坐阶前树下以“长毛”事谈古如常。
《呐喊》14篇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辛亥素描,主角均是生存在鲁镇的庸众。《药》中夏瑜的原型即秋瑾,这一场孤寂的革命独角戏,被民众们兴奋的传说欣赏着,革命者就义的鲜血成了民众愚昧的药引,治疗与被治疗的过程均被另一看不见的文化逻辑所主导,最后的结局却是坟——他们都被莫名地吃掉了。
《阿Q正传》透过辛亥革命在未庄的传播,呈现了农民对革命饱满的想象——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革命党的武装是白盔白甲,穿的是崇正皇帝的素,他们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来叫“同去,同去!”革命成功就是自我的膨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然而,革命在未庄的实际发生却是赵秀才与钱洋鬼子砸了静修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将老尼姑当作满政府,在光脑袋上给了不少棍子和栗凿,并不许在最底层苟活的阿Q革命,最后将他送上刑场——被狼眼睛一样可怕的庸众目光吞噬了。
《头发的故事》以讽刺笔法表达了对辛亥革命的另类纪念,作者借N先生之口说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然而,“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风波》传播的是“皇帝要坐龙庭了”这条消息,通过张勋复辟在鲁镇的小村庄引起的村民心理恐慌,彰显了辛亥这场停留在辫子上的革命,于民众的内心丝毫不触及。
《彷徨》集没有直接状写辛亥革命的篇章,却突出了辛亥时代力图改革的知识分子——实际就是鲁迅自己。如吕纬甫、魏连殳都是百姓传说中“吃洋教”的“新党”,或是曾外出游学又回到故乡的教师,革命前无不敏捷精悍、议论奇警,满腔热情,在口口相传的舆论场中却是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永远是冰冷的,但他们是有趣的话柄,民众们从欣欣然打听新闻,到遭了魔似的发议论,再到小报也匿名攻击,学界也有流言,最后到无趣,因为生命同时寂灭了——吕纬甫发现自己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从此敷敷衍衍,教些“子曰诗云”来糊口;魏连殳则是在凄冷的夜里孤独地死去。
是什么吞噬掉了这些鲜活的生命?这看不见的文化逻辑是什么?正是鲁迅所说的无知无勇无理性,单有怨愤的危险的“气”,一遇国民卑怯的坏根性,便消散于无形。
《范爱农》中,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被挖心炒食后,留日学生中群情激昂,准备拍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而范爱农独冷静超然,以为于事无补,没有意义。对此,“我”的胸中立刻涌上一股“气”——“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种个人意气联结着阿Q的“革这伙妈妈的命”“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联结着秃先生的私塾、华老栓的茶馆、公务员的寓所、临河土场的家庭餐桌、咸亨酒店等舆论场所的文化气场,联结着整个民众的心理结构,直到1927年,当鲁迅在中山大学演讲,被称为“战斗者”、“革命者”时,听到“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很多人幻觉中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却无法心安理得,乃至忘乎所以,而是自然而然联想到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被身不由己地捧到战士的高度。于是,转而涉笔调侃到,莫非自己也非“阵亡”不可么?。
如果说,鲁迅小说中因重在凸显国民文化心理,而颇多夸张和讥刺,那么对辛亥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明确的表述和评价则集中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可以整理出系统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当年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失败的战士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前驱。“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多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而“首举义旗于鄂”的武昌起义之能发生,则是宣传的功劳,“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中国“确实光明得多”,“将来很有希望。”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二百年的君主统治,开始向“人道”迈出一步,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因而应时时缅怀革命“先哲的精神”和先烈们的献身精神,不断弘扬,使之“活在战斗者的心中”,此后他的文字中再也难见这样发自肺腑的称颂之言。
鲁迅笔下更多的是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他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是因为“排满”“光复”的宣传口号,既迎合了激进青年的“复仇和反抗之心”,又迎合了保守人民的“复古”心理,因而易得响应。然而,后来并未恢复“汉官威仪”,亦无“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许多人也就因此失望或转为反动了。以后较新的改革,着着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最终被奴才主持了家政,内骨子当然是依旧。辛亥革命成了“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孙中山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和袁世凯妥协,于是种下病根,上演了一幕幕轮回的丑剧。革命党一派绅士们所深恶痛绝的新气——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仿佛惟独自己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而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绅士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按:指革命党),一路的呵。”于是,又“服了‘文明’的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乃为旧党所乘。“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的秋瑾,便死于告密,旋即无人提起。王金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
这样的革命现状,顺民们如何能有新面貌?墮民不但安于做奴才,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学术界仍守着清初的“奴才家法”。鲁迅怎能不感到,革命以前,自己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许多民国国民反而成为民国的敌人,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意中别有一个国度。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一切均渐渐坏下去。其实,“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让人“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而在鲁迅看来,革命者应该充足实力,各种言动宣传,只稍作辅佐即可,大肆渲染,只有煽动气盛,少乏理性,与民族坏根性结合,更易发生极大的流弊。遍览当时各种主义者的精神资源,其实都是旧货,因而自己宁肯无所属,保持独立,渺茫地寄希望于革命者能够自己觉悟,自动改良。
鲁迅临终前的绝笔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为纪念辛亥革命25周年而写的未完稿,缅怀了章太炎先生等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先导者和其他革命先驱者。文末提到黄兴时写道,“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这一段描写,就是鲁迅三十年创作生涯中的最后几行文字。
鲁迅在革命扑面而来时的深邃冷静,不是没有被视为怯懦,他的纸上苍生,笔墨冷嘲,不是没有招来鄙夷和批评——“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鲁迅偏不给那些最适宜生存的人提供“大卖消息,大造谣言”的材料——以白白献出生命的方式。
鲁迅的辛亥情结甚至使他成为创造社青年眼中的落伍者——“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辛亥记忆成了“骸骨的迷恋”。辛亥的确是鲁迅一生无法取代的重要时空坐标,当革命发生时,已是而立之年的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立场,对后来一代是一个传说,对于鲁迅,却是用笔墨干预过时政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而追求思想革命的辛亥使鲁迅找到了归属,真正理解了革命的内涵,才于之后奉献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真知灼见。
正是因为幻想过,高兴过,才能深味革命其实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革命不只是为了获得民族的自由发展扫清政治上的障碍,不是让人去死,而是为了让人活。革命者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革命有血,有污秽,但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鲁迅辛亥书写的反讽之镜,是映照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是从革命志士血犹未冷的手中接过来继续长鸣的警世钟,而不是无关痛痒地指摘过气的英雄,字里行间即便幽默一下,都是悲悯的。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战线和作战方式与策略。对于斗争武器——匕首投枪式的短文,他也有深刻的反省——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好用反语,迎头一击,稍一不慎,简练流于晦涩,常招误解于大出意料之外。
他同样景仰革命党人的勇敢赴死,不然,如何会呼吁去做一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当看到人们已然踏着烈士的鲜血热闹地欢庆节日时,当看到国民政府征集革命文物,竟把邹容的革命史列入了“落伍者的丑史”时;当听到“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的南京民谣时,他分明是忧心如焚的,他担心烈士的鲜血成为“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悲壮剧”,“都被人们踏灭了”,“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鲁迅之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他并不是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也不是叫别人去牺牲,自己冷眼旁观;他不幻想文学对于革命的伟力,也不要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做高妙的幻想,而是志在做思想文化战线上清醒的革命人,以战斗的文章,奉献辩论的生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治麻木状态的国度,时刻警惕和反抗自我的苦闷,努力减少赏玩、攀折,摘食革命果实的愚民。
革命者抛洒热血灌溉自由树,思想者呕心沥血发出现代的自己的声音,为了唤起民众,消灭专制,踏上民主自由之路,获得社会的长足进步,他们均以天下为己任,给出全部的生命,共同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
鲁迅的辛亥远远没有成为往事。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