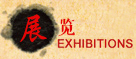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刘静
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即一层的22号室),曾经聚集过一批热情的青年人,他们将亲自撰写的或者是志同道合者所写的文章、诗歌编辑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叫《新潮》的杂志,大力鼓吹新文化,新思潮。这杂志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在一个月内就再版了三次。这紧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的小房间,就是新潮社的社址所在,这几个青年人,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青年的代表: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顾颉刚、杨振声、俞平伯等。他们在红楼内创设的新潮社和《新潮》杂志是《新青年》最坚实的同盟军,与《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一、“新潮”激起
自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校园内有了活泼清新,学术繁荣的氛围,也就为新青年们的成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的傅斯年和顾颉刚,以及他们的邻居徐彦之,顾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傅斯年的朋友罗家伦,这几个年轻人因志趣相投每天都聚在一起闲谈。谈话中他们觉得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应该自己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才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而且他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因此在当学生的时候,办杂志可以练习一回。[1]这件事成了他们谈话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了。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论不休以外,新建成的北大红楼也逐渐成为青年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据罗家伦回忆,他们在红楼的据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红楼二层的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也是一个另外的聚会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2]
群言堂和饱无堂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当时只有在北大红楼内才能出现,钱玄同、李大钊等新文化的倡导者与热情、活跃的青年学生之间貌似闲谈,实则进行着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旧学功底都十分深厚,深得黄侃等旧派学者的器重,但是在《新青年》和新文化学者的启发下,也毅然投向了新文化派。
同时,“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着两个房间。”[3]李大钊“曾给过《新潮》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然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4]由于工作关系,他可以和许多热心时事,常到图书馆借书、阅览的学生有更多的接触,他的许多进步思想也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青年们。正是由于红楼内师生们畅所欲言的环境中,各种新思想、新风尚在新青年们中间广为传播,也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无拘无束谈论的基础上,更激进的青年们开始不太满意《新青年》的一部分文章,他们开始考虑: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
青年们这个办杂志的想法,也经过了多次讨论,但大都因为经费方面的原因而搁置起来,后来徐彦之提议可以请求学校的支持,就和当时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5]这让几个青年喜出望外,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这个名字是由罗家伦提出来的,而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是由徐彦之提出来的,按照“新潮”两字的意义,译作“New Tide”,但是印在书面上的英文译名是“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年青人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西洋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的名词,就是“文艺复兴”,是欧洲在中古黑暗时代以后,解除种种经院教条的束缚,重行研究罗马,尤其注重在希腊文化的时期。这是西方文化最早的曙光。后来也有学者认为这本杂志定中文名为“新潮”,大概来自1904年创刊的日本启蒙杂志《新潮》,那是一个“旨在恢复和深化十九世纪启蒙学者的精神”的刊物。
当然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来说好由学校出资,但是北大杂志团体方兴未艾,“一时出了几个,更有许多在酝酿中的”,校方不可能一一补助,但又不能过失公平,“于是乎评议会议决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 但是傅斯年等人写信给评议会,强调《新潮》销路很好,而且学校答应《新潮》出资在前,议案在后,最终评议会同意维持以前的方案,即“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附设的印刷局负责”,“银钱出入由学校会计课负完全责任,社的干事概不经手银钱”。[6]《新潮》经费比起《国民》和《国故》来都充足和稳定得多。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主其事者,大部分是《新青年》的同人。《新潮》从人员组成到出刊宗旨,都与《新青年》最为接近。领导者也很受学校负责人的赏识。许德珩曾回忆说:“《新潮》和《国民》不同,是受到校方支持的,学校每月给《新潮》四百元,并在校内挂牌子。它比《国民》筹备晚,却能在同一天出版,这都是因为有胡适帮忙。” [7]胡适对《新潮》的创办“出力最大”,评议会能够维持对《新潮》资助的原案,胡适在其间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胡适做了他们的顾问,李大钊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拔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校长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写“新潮”两字。正是依靠校方和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才能维持创办时“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资助”的初衷。
二、“新潮”风尚
《新潮》是追随和摹仿《新青年》的,但是他们对《新青年》呼吁政治改革的一面并不感兴趣,而是主张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的成员开第一次预备会的时候就确定了这份刊物的三个原素:(一)批评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文词。[8]正对应着《新青年》广告上声明的四种主义:(一)改造国民思想;(二)讨论女子问题;(三)改革伦理观念;(四)提倡文学革命。
《新潮》一直以学生刊物的面目出现,《新潮发刊旨趣书》给自己的定义是:“《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新潮》发起者希望通过这份杂志“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这样可以养成“自别于一般社会”的学校风气,最终达到通过大学的思潮去影响社会的目的:“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9]
他们为这份刊物规定的“四大责任”,更是处处以《新青年》为榜样,又时时注意自己学生刊物的特色,除要“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和谈论社会“因革之方”外,《新潮》的责任还包括“鼓动学术之兴趣”和“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10]前面两种责任,实际就是《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社会改良”,后面两种,才是《新潮》的独到之处。《新潮》的政论文章不太多,大多数是文艺作品。罗家伦自己就说过:“《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警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廊,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11]
三、《新潮》发行
新潮社的出版品一共有三种,即《新潮》杂志、《新潮丛书》及《文艺丛书》。《新潮》杂志第一期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就再版了,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有这样大的销数,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计划,《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后面的则常有拖延,时断时续,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第3卷总共只出了2期。第1期发行于1921年10月,第2期发行于1922年3月,中间整整相隔了5个月,而这,也是《新潮》向历史奉献的最后一期杂志了。刊物之所以不能按期正常出版,除了“五四”运动的短暂耽搁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稿源方面的,社团成员总共40余人,竟有30多人出国在外,忙碌的留学生活使很多社员无暇写稿,而留在国内的一些社员,如叶绍钧、朱自清、孙伏园、郭绍虞等人,又分心于文学研究会上的事情,稿源不济;二是经济方面的,虽然《新潮》的销路很好,但回款并不及时,北大垫付款项也不能按时支付,而且1920年新潮社又开始出版书籍,无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资金,因此,杂志出版就只能向后延期了。《新潮》一共出版了12期,历时2年零5个月,最终无疾而终。
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在红楼的“文科事务室”举行全体社员大会,除了改选职员外,还决议将该社从杂志社改变为学会,并正式启动丛书的出版。[12]经过短期的筹备,《新潮丛书》一共出了六种书刊,即王星拱编著的《科学方法论》,陈大齐(百年)著的《迷信与心理》,周作人翻译的外国近代名家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册),新潮社同人编辑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陶孟和著的《现代心理学》,李小峰、潘梓年译的《疯狂心理》。自周作人任主任编辑以后,学会的出版重点转向了《文艺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如冰心的《春水》、鲁迅的《呐喊》等。
《新潮》杂志出版后大受欢迎,各地的代销处也日渐增多,个人、学校、报社、图书馆、教育会、学校附设的贩卖部等经售代销的居多数,甚至有绸缎庄代销的。到1919年10月,全国代卖处竟达40余处,但即便这样,“顾客要买而不得的很多,屡次接到来信,要求重版。”[13]这不能不说是发行上惊人的成绩。
四、“新潮”反响
《新潮》内容激进,形式新颖,又挟《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之威,所以内容形式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顾颉刚回忆:“《新潮》出版后,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以看到。因为《新潮》中的文章多半是青年人写的,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14]《新潮》的出版,无疑为已经启动的白话文浪潮推波助澜,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的《社告》中,明确要求投稿者注意:“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句读须用西文式。”“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话新体为限。”[15]《新潮》以后,《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白话刊物纷纷出版,《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也逐步改用白话,短短一年中,竟然“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
《新潮》杂志一直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它与《新青年》一起,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二新”。作为一种纯学生办的刊物,《新潮》更有一种青年学生的激进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以至遭到不少的反对。但这样并不影响《新潮》在青年们心中的地位,反而更增添其几分反抗旧传统的勇气和力度。
继《新潮》杂志之后的《新潮丛书》和《文艺丛书》,虽然出版形式上与《新潮》有别,但在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上却是前后统贯,一脉相承,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两套丛书中,不管是撰述文字,还是翻译作品,不管是名家名篇,还是新人新作,都以原创和革新的面目,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在那一时期的出版物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冰心的《春水》,鲁迅的《呐喊》,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李金发的《微雨》,皆为作者的处女作,独具艺术风采。这些作者后来都有重大的发展,他们的风格产生了影响,甚至还形成了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奠基和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诞生和发展都与北大红楼息息相关,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在红楼内汇合,形成一股荡涤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新潮流。
--------------------------------------------------------------------------------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
[2]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3]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4]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5]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30日。
[6]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30日。
[7]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37-38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8]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30日。
[9]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
[10]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
[11]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
[12] 见《北京大学日刊》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版,《新潮社纪事一》。
[13] 《启事》,《新潮》二卷一号,1919年10月30日。
[14]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5] 《社告》,《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