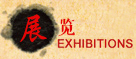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陈翔
北大红楼,曾因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而蜚声海内外,铭刻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光荣历史,为动荡时期的中国谱写了值得骄傲的乐章。然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古老的北京城,北京大学一度被强行占用,成为侵略者进行殖民统治的基地之一。曾象征“民主”、“科学”的北大红楼在这个时期却记载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
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后,形势虽然紧张,但是北京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根据1937年3月7日《北平晨报》刊登的消息,这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共计学生1031人,其中文学院394人,法学院244人,理学院362人,研究生19人,各系旁听生12人。5月25日,《京报》报道,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年内将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四处联合招考新生,两校命题委员会各10人已交换命题意见,联合招考的其他事务工作也在进行中。北平的联合招考,考场设在故宫博物院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殿试”。考题已经拟定,等待印刷。北大的教职员工们,正忙于向宫中搬运考试用的桌椅。然而在这一工作进行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北平城外枪炮声不断,但并没有使联合招生工作中止。7月10日,北大、清华两校考试委员会负责人从上午8时到下午7时半,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监印了新生试卷12000份;13日,又监印了北大研究院的试题,并评阅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庆赐的初试卷。16日,中国文学系的新旧助教办交待,系主任罗常培给新聘的助教吴晓铃、杨佩铭规定约法十二章。19日,又和魏建功、李晓宇等人在文科研究所会商北大所藏甲骨卜辞付印事。[①]直到7月29日、30日平津相继陷落后,这些工作才被迫陷于停顿状态。
进入8月,北平的政局发生了重大转变。6日,伪北平市政府成立,江朝宗任市长。因张自忠潜行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废止委员长制度,而以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五人负责处理一切事务。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2000多人进驻北平城,占据天坛、旃檀寺、铁狮子胡同一号及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10日,上海《申报》登载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招考委员会上海办公处通告:因平沪交通阻断,试题短期不能寄到,考试再延期举行。
“殿试”不能如期举行,北大的桌椅却没有从故宫搬回。当时谁都没有把时局看的有多么严重,认为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正值暑期,学生放假。北大的教师们,依然每天到学校上班。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受邀参加。7月8日,北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到位于米粮库4号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家中,与张奚若、徐森立等一起,聆听了胡适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事态不会扩大。这天下午,他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开会,随后到庐山参加谈话会。这样,当日军进驻北京大学的时候,支撑学校的重大责任就落到了秘书长郑天挺肩上。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北大同仁纷纷南下避难,留在北平的人,就把郑天挺当作主心骨,常常到他这里打听情况,交换意见。
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南迁到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后,即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留在北大的教授还有70人左右,以及年轻一些的讲师和助教。蒋梦麟、胡适都没有消息来,大家经常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局面。8月13日上午,罗常培邀集马裕藻、汤用彤、孟心史、毛子水、邱大年、陈雪屏、魏建功、卢吉忱、李晓宇等,在第二院校长室商议维持校务之事,决定在离开北平之前,协助郑天挺共同支撑残局,低薪的职员暂发维持费30元。
8月中旬后,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屡次到北大校园进行骚扰。25日,日本宪兵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郑天挺独自去支应。同日,汉奸组织的地方维持会约集北平各校负责人谈话,命令各校将保管各项加封,然后由维持会派人核查。9月3日,秋雨蒙蒙,日军进驻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和灰楼新宿舍,对北京大学部分建筑进行强行占领。
当时,刚刚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并被留系当助教的吴晓铃,亲自经历了红楼被占领的过程。他回忆道:
“一到红楼门首,就见情况不对,出去的人多,进来的人少。楼前偶语者都是‘斋夫’(即工友),未见教职员。这时,冉德老人(国文系的工友,笔者注)在人丛中见到我,挤过来,说:‘吴先生,日本人中午进占,您在这儿呆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我说:‘不行,咱们得把办公室清理一下!’我们上了三楼,一眼瞥见佟山老人(文学院院长胡适办公室的工友,笔者注)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前,两眼里搁着还没有掉下来的泪,看到我们,就跑来帮助整理系办公室,我把系里的师生名单、照片和工作日志等文件检出,放在书包里;又把书籍分别包扎,写了个草目;出来,用木条把木门钉牢;然后又帮着佟山老人把院长室清理一过,封了门;路经《歌谣周刊》编辑室,进去捡了几篇稿子,也封了门。我把各办公室和课室门上被日军用粉笔标的分驻番号抄了下来,记得院长室是‘南队长室’,这才和两位老人下到一楼,一看,楼里楼外,渺无人迹,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好不凄凉!我要去罗主任家里报告,写一个条子给四斋的老王,请冉德老人交给他,把宿舍里我的行李送回家去。正写时,忽然听到楼外靴声阵阵,佟山老人说声‘不好!’我们跑到一楼正门,果然看见几辆卡车停在校外马路上,校门已经布上荷枪岗哨,一个佩刀的眼镜小胡军官带着几个兵向校内走来。我们便成最后告别红楼的二老一少。”[②]
自1937年9月起,日军把北大红楼及周边建筑作为驻兵之地。红楼的产权虽属于北京大学,但北大却几乎失去了对红楼的支配权。而且,驻扎在红楼地区的日军部队很庞杂,换防较为频繁,红楼安全没有保障。
同年11月,驻扎在红楼的松井部队在开拔之后,红楼曾出现暂时的空虚。经常有人在白天翻墙入内,盗走红楼内国学研究所的许多古物。北平地方维持会要求警察局认真巡查,严格管理。警察局即在北大第一院墙外加设岗哨,并在红楼大门前添设活动岗位,注意门禁。“且与该院庶务包尹辅接洽,所有校内各处,均由校警负监守之责”。[③]
两个月之后,日军小林部队撤出,德川部队进驻。时北大校警王远峰、王宝崑、张玉、王忠、赵声等五人从北京大学第一院内携六罐机器油出门被查获,遭到指控。北平警察局判处王远峰、王宝崑、张玉等三人徒刑,王忠、赵声进“感化院”接受教养。[④]
由此可见,在日军进驻北京大学后,红楼成为日军的营地。从我们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北大红楼至少曾有松井部队、小林部队、德川部队陆续驻防。而在换防期间,负责安全保卫之责的是北京大学校警。
1937年11月中旬,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包尹辅等陆续离开北平,经由天津、香港,转赴长沙。此时的北京大学,几乎已人去楼空。北大残局,交由周作人、马裕藻、孟心史、冯汉叔四位“留平教授”负责,每月寄给50元津贴费,他们的职责是看管好北大的校内产业。但此时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开始打北大的主意。据周作人回忆: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⑤]。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⑥],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同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⑦]
这样,在1938年春天,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的红楼,实际已决定让出而交给日本宪兵队使用了。
11月8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颁布命令,通知本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及分队等迁至东城汉花园北京大学第一院。同时颁布各机关开始业务工作的时间表。即:11月8日,日本宪兵队司令部;11月10日,北京宪兵队本部;11月12日,北京宪兵分队。[⑧]
几天后,北京[⑨]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局长余晋龢颁布训令,为北京宪兵分队开送电话番号。电话总机为东局5461至5467,通过总交换局,可以接通以下各室,其分机是:分队长室——二八番,将校室——三O番,庶务室——二九番,特高室——三一番,警务室——三二番,司法室——三三番,受付室(夜间)——三四番。[⑩]
因此,在1938年11月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北京宪兵本部、北京宪兵分队同时驻扎红楼办公。宪兵分队下设分队长室、将校室、庶务室、特高室、警务室、司法室、受付室(夜间)等机构。至于宪兵队司令部、宪兵队本部的机构设置,以及司令部、本部和分队相互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考证。
二
日军占据红楼,并作为其宪兵队机关之后,便在地下室开辟了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拘留所)。与昔日书声朗朗的北京大学校园相比,红楼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因从事抗日工作而被捕的北大校友曾回忆道:
汽车一进门,看见巍巍的红楼,仍然如故而人物全非。六年读书的场所,五年未离的母校,自“七七”后,过门而不得入者三年,今日又来到,不觉大有今昔之感。从前的号房成了宪兵卫室,楼前两旁的篮球场,筑成一个一个的日本式板房。一进楼门,昔日公布课程表的木框不见了,只看见两旁小窗,敌人的号房和传达室。[11]
根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在进入红楼后,从东侧的台阶下去,是一条甬道,两边均是单间房。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是拘留人的囚室;往东是刑讯室,即敌人对犯人灌凉水和拷打的地方。单间的建筑工料精细,隔音,里面的声音不易传出。一进屋门只有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迎门和左手两面全是用六七公分粗的四棱木排成的木栅。正面开了一扇一米高、半米多宽的笼门,笼门右下方留了一个能送进饭碗的小洞。左手方向的木栅下面有半尺来高、一尺多宽的木门锁着。笼子上下左右全是木板包镶,板缝是榫子活。所有木活,全是白茬,不上油漆,表现出日本建筑的风格。唯一的一盏电灯,装在笼外屋门内的那一小块房顶上。小木笼门的里面,放着一只约半米高的椭圆形马桶。余下约四米见方的地板,是被押人员呆的地方,人多时要容纳20多人,坐着还人挨人,睡时侧身躺都困难。[12]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投资创建的燕京大学即遭日军查封。校务长司徒雷登遭日本宪兵逮捕,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美国兵营中。此后,他曾四次被带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受审。[13]燕京大学的20名师生也相继被捕,并被押解到红楼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日本宪兵一一登记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居址、年岁、相貌特征。“并为貌其形状,如发之长短,五官方位,须之有无,皆备载之。凡所携物,如帽、围巾、裤带、腿带、时表、钞票、字据、纸烟、火柴、小刀、笔,皆不准携带,一一入籍,代为保管。”[14]随后,捺下指纹,驱入地下牢房。牢房的规定很严格,墙壁上张贴着用中、日文书写的规定:不得谈话,早晚八时寝兴,白天应盘腿端坐,不得斜卧,不得靠墙,衣被要叠放整齐。早上只有一盂麦粥,一杯白水、一点儿咸菜;午餐有两个馒头,一碗汤菜,一碗白水;晚上的饭食和中午差不多,萝卜、豆芽、白薯、菠菜汇在一起,白水煮熟,略有一些咸味。
相比之下,被关押在牢房里的日本人、朝鲜人却享受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有棉被褥,三餐皆有米饭,并有大酱汤、牛肉、土豆和洋葱等。日本看守可以无故抽打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与被关押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发生争执,就要惨遭毒打。
被捕的许多教授,如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陆志韦等,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邓之诚回忆他亲身见闻时说:
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蹴之,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至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不识确否。然入宪兵队后而无下落者,往往有之,大约用刑分队尤严,往往中夜闻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15]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红楼地下室内没有取暖设施,人人“冻极而僵”。由于狱中营养和卫生条件太差,又缺医少药,以致狱中传染斑疹、伤寒等病,造成数十人死亡。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大多病倒,虽幸而未死,却个个骨瘦如柴,几无人状。更令教授们无法忍受的,是日本宪兵和看守兵对他们的任意凌辱。宗教学家赵紫宸两次乘囚车赴日军司令部受审,加手铐系白绳,车过大街稍一瞩目,押解兵就用刀背打他的头。哲学家张东荪饥饿难忍,向日本翻译请求吃点东西,备受嘲弄:知道这是坐牢吗?还想吃饱饭!一次,张东荪与邓之诚谈话,被看守兵发现,遭到申叱,一个看守兵提一桶水过来,招呼张东荪走到门洞前,忽然把一桶凉水泼向他,浑身上下衣服湿透,冻得他直打颤。
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牢房的,还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从事抗日活动,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候仁之在天津被捕。日本宪兵将其解送到北平,未经审讯即被押到红楼地下室的一间牢房,与燕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时名孙以亮)关押在一起。当时,孙道临是由于在校内参加有抗日题材的话剧演出而遭到逮捕的。两人原本相识,见面后彼此又惊又喜。孙道临帮候仁之在地上铺好毯子,两个人躺下后,头部紧靠在一起,由于地方狭小,两个人的腿脚尽可能各自伸向另外一个方向。为了方便谈话,孙道临要候仁之把一块手巾蒙在脸上,做出掩饰灯光的样子,实际是为了避免日本宪兵窥见他们谈话时的脸部的活动。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分别被关押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房里。每天上午,每个牢房各出两个人,由宪兵押着抬起恭桶排队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时,可以见见面,偶尔在过道的转弯处,也可以小声地传递一点消息。
留在北平的北大教职员除了个别人之外,大都抱着“誓饿死不失节”[16]的信念,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的铮铮骨气。北平的知识分子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始终不断。北大红楼地下牢房就成为日本侵略者迫害爱国志士,试图从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斗争意志的场所。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在日本兵开进北平的时候,做好了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心理准备。他拿起铁铲跑到街上,对一队队日本兵怒目而视,遭到日本兵的毒打。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蓝公武公开宣传抗日,大讲世界形势,大讲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听他讲课的人越来越多,场场爆满教室内外,也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1940年夏的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越墙而入,闯入蓝宅,将蓝公武父子三人抓到红楼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蓝公武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一次,日本宪兵审问他,一个翻译不知是要帮他还是不耐烦,就把蓝公武的答话故意译成认罪的意思。蓝公武精通日语,他听后,立即暴跳如雷,用日语骂翻译“混账!”质问:“为什么故意歪曲我的意思?”日本宪兵大佐听他能说流利的日语,又得知他在日本留过学,就对他客气起来。不久,蓝公武被释放出狱。他在日本宪兵队被关押了九个多月。
红楼地下室的“留置场”,实际是日本宪兵队的拘留所。关押在这里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从事抗日活动的北平各高校爱国教授和教师、学生外,还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及从事谋刺日伪汉奸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有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也有一些小商小贩;还有犯有过错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根据不同情形,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不一样,有几天的,也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他们通常在“留置场”内等待审判。日军在华北的最高军法机关叫多田部队军法部,设在铁狮子胡同西口路北。被关押在红楼的人,都习惯称那里为“军法会”,它负责审判从华北各地解来的抗日人员和日军、汉奸中的违纪人员。1942年2月,大批日本宪兵涌入红楼地下室,将陆志韦、张东荪、邓之诚、赵紫宸、侯仁之等11人押解到“军法会”受审。此时,他们已在红楼地下牢房生活了两个月了。在法庭上,陆志韦等人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没有占到丝毫便宜。6月18日,日本军事法庭做出裁决:抗日本应处死,姑从宽省释,今后若再抗日,必处死不贷。洪业、邓之诚、刘豁轩无罪开释;赵紫宸、陈其田、林嘉通、赵承信处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侯仁之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张东荪、蔡一谔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三年;陆志韦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二年。同时规定,在服刑期间,无任何迁居旅行的自由,随传随到,有事必须外出时,事先应以书面报告方式,说明外出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批准后,方可成行。[17]
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京大学使用。但在沙滩广场北面的楼里,还依然驻有少量的日军。侵略者蹂躏红楼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据当时进入红楼上课的学生回忆:“日本宪兵队是从学校撤走了,但熄了火的烧人炉还耸立在红楼后边广场东墙下的衰草间,墙壁上黑糊糊的烟熏火燎;红楼地下室白墙上还飞溅着被关押拷打中国人时的斑斑血迹。”[18]
人们印象中的红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象征。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却让这座红楼充满了黑暗与恐怖。地下室的日本宪兵队监狱,是侵略者践踏中国领土、屠戮中国人民的历史铁证,同时也铭刻着爱国志士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事迹。
--------------------------------------------------------------------------------
[①]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151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②] 吴晓铃《居京琐记》16—17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③]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092
[④]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3—04088
[⑤] 孟心史于这年的1月14日病逝。
[⑥] 汤尔和(1878-1940)时在汉奸组织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主管教育
[⑦]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559—560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⑧]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358
[⑨] 1937年10月,日伪政府改北平为北京,但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
[⑩] 现存北京档案馆资料 J181—022—01360
[11] 郭海清“悲喜交集话红楼”《北大校友通讯》1943年第一期,13页
[12] 冯纲“敌伪监狱见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324-325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
[13]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45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8月版
[14] 邓之诚“南冠纪事”《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5] 邓之诚“南冠纪事”《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16]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 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157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17] 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146页 杭州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8] 史会“窗外柳——红楼生活片断”,《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4期56页,1998年5月。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