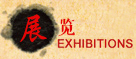论嵇康及魏晋风度及其他 刘思源
发布日期:2015-07-20 浏览数:
上大学的时候,不知在一本什么文选上,读到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那时就觉得这位嵇康先生未免太矫情了。山涛(字巨源)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有一个时期,他们还有阮籍、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经常在山阳的竹林高谈阔论、诗酒逍遥,结成有名的“竹林七贤”。山涛升迁了,没有忘记老朋友,于是向朝廷(实际上是司马氏集团)推荐嵇康来接替他原来的职务吏部郎(注意,这可是荐拔官吏的官,所谓“要路津”,是一般人削尖脑袋钻谋的美缺),这是何等美意,揆之“苟富贵,毋相忘”之义,他是很够朋友的了。嵇康不接受也就罢了,不必好像受了莫大侮辱似的闹什么绝交。绝交也就罢了,不必“七不堪、二不可”地来这么一大篇绝交书,而且话还说得那么难听,什么“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羶腥”,极讽刺挖苦之能事。总之,不受抬举,反而骂人,刻薄有余,忠厚不足,朋友之道,似乎不当如此。因此,他的文章虽然写得极有气势,极有文采,然而对他的名士脾气我却不大喜欢。
后来书读得多一点,对嵇康其人及其时代知道得多一点,最初那点恶感消释了,对嵇康的名士脾气也越来越理解,越来越佩服,现在则简直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发其狂士之高致,不如此不足以标其超迈峻洁之人格,一句话,不如此嵇康就不成其为嵇康了。
鲁迅有一篇名字很长很怪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学史(说是文化史也无不可)随笔。它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胜义叠见,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历史概括力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叹赏不置。在这篇讲演中,鲁迅提出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我大胆地作了进一步的推导:魏晋不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自觉、美的自觉———合而言之,就是对于人的审美的自觉———的时代。
其实,早在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就很盛。不过,那时品评的范围很小,主要集中在道德方面。品评的权柄,操纵在少数长吏及号为人伦之鉴的品评家的手里。到了魏晋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品评人物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而泛及人的所有方面。品评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整个名士阶层的习尚。更重要的是,品评的眼光不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政治的、道德的,而是审美的。魏晋风度,这个极富审美意味的概念,就是对那个发现人的美、欣赏人的美的时代的准确概括。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魏晋多“美人”(不是指美女,而是指美男子),有“面如傅朱”的何晏,有被人“看杀”的卫玠,有一上街便被妇女们“连手萦之”的潘岳,有号为“玉人”的裴楷,有“轩轩如朝霞举”的司马昱,有“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美人之多,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美男子的总和,可以说魏晋是个盛产“美人”的时代。这当然不是因为历史偏爱它,所以让它格外出产美人,这种情况恰恰是由当时流行的审美性的品评人物的风气造成的。
嵇康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门第不高。他的父亲做官只做到太守,死得又早,使他早早成为孤儿,靠母兄抚养长大。他似乎很有志气,通过自身努力,居然早早成名。那是一个名士时代,一成名士就无所不可。凭着少年名士的名头和“龙章凤姿”的品貌(他也是有名的美男子),嵇康得以与魏宗室联姻,娶了魏沛王的女儿长乐亭主。婚后,做了郎中、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但中散大夫并不是什么正经官职,无职无守,也许有一份干俸吧,因此,他得以与阮籍、山涛们结成竹林七贤,在山阳自在逍遥地度着他名士生涯。假使处在太平盛世,他也许会就此名士风流下去吧。然而他处在魏晋改朝换代之际,政治环境极其险恶:一方面司马氏集团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准备迫使曹魏王朝“自觉”禅让;另一方面,曹魏集团不甘被禅代的命运而作最后挣扎。嵇康是魏宗室女婿,因此天然地属于在这场斗争中没落的、必然被取代的曹魏集团,因此也就天然地处在司马氏的政治迫害之下。
当年,曹操就是通过他攫取的权力,迫使汉王朝“自觉”禅让的。而今,司马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其残酷性远远过之。曹操并不怎么杀人,只杀了两个名士。一个是孔融,一个是祢衡,祢衡还是借黄祖之手杀的。这固然是因为曹操雄才大略,懂得爱惜人才;也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格局未定,需才孔亟,如果不善加笼络而肆行杀戮,无异驱逐人才以资敌。司马氏则奉行赤裸裸的杀人政策,他们杀何晏,杀夏侯玄,一直杀到嵇康,杀了一百多个名士还不肯歇手。或者要说,当时有些名士闹得太不成话,败坏了纲常伦纪,沦为名教罪人,所以要杀杀他们,以挽世风。这是皮相之论。胡闹是名士的特权,也是名士的标记,不胡闹就做不成名士。司马氏在这上面倒是相当优容的。清谈没关系,喝酒、吃药没关系,甚至“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态,同禽兽”也没关系。这都是小节,小节出入可也,但大节不容含糊。什么是大节呢?大节就是政治,就是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的搏斗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这才是司马氏集团为名士们设立的“dead line”(死线),犯者必死。
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下,一种混世保命的哲学在名士当中流行。不过,那时不这么叫,而美其名曰“慎”。李康在他的《家诫》中说,为官之道有三,曰“清、慎、勤”。又说“清、慎、勤”当中,“慎乃至大”,万不得已,“清、勤”可弃,“慎”却决不能丢。“慎”俨然成了最高德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慎”能保命。据说,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昭许他为“天下之至慎者”,所以他保住了性命。又据说,嵇康也是个“慎”者,然而他的“慎”贯彻得不彻底,在最关键的政治抉择上不“慎”了,所以丢了性命。
司马氏并不胡乱杀人,他们只是用杀人的手段,为名士们指示一条出路,告诉他们生之所在,死之所在。面对这样的高压,名士集团很快分化成三派。一派以嵇康为代表,他们不识时务,不知顺逆,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可称为反对派。一派以阮籍为代表,他们明哲保身,与司马氏的关系若即若离、半推半就,可称为中间派。一派以钟会为代表,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甘心为司马氏所用,可称为司马派。让我们先来看中间派,看阮籍。
阮籍可说是那个时代最痛苦的人。嵇康、钟会他们对待司马氏的态度虽然相反,但都心意已决,不再徘徊瞻顾,而阮籍就难过了。他既不愿卖身投靠,又要与司马氏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个中分寸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好在他有“至慎”的法宝,又能装酒糊涂,司马氏想招他为婿,他居然能大醉六十日不醒,使得提亲的人无法开口,只好作罢。然而镇日临深履薄,战战兢兢,其精神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才会“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方,“辄痛哭而反”;才会“好作啸”,没事经常往苏门山中仰天长啸。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行,其实都是他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痛苦出诗人,作为他“苦闷的象征”的咏怀诗,居然在文学史上放一异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学成就。
嵇康虽然是名士领袖,但在曹魏集团中并不是什么重要脚色,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说到底只是一介名士而已。所以司马氏对他一直采取笼络的态度,所以钟会才会一再要与他结交,山涛才会推荐他做吏部郎。尽管他有些把柄———比如写文章,发怪论,其间不无影射司马氏之处;又比如他曾想起兵响应毋丘俭造反,司马氏也不纠缠计较。然而他却不知好歹,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地、坚决地宣示了他对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这才走上了死路,他曾经得罪过的钟会就是送他上路的人。
钟会出身高贵(他的父亲钟繇官居太傅),成名很早,文武兼资,是司马氏集团的心腹谋士,时人比之为张良。钟会只比嵇康小一岁,凭他的门第、才能、名气,要与嵇康结交,不说是折节下交,至少也不算高攀。但这位仁兄在嵇康面前似乎格外气短,怎么看都像是巴结。一次钟会巴巴地从洛阳跑到山阳,专程拜访嵇康。其时,嵇康正与向秀在树下锻铁,看也不看他一眼,话也懒得跟他说一句,只是在他要走的时候才挑衅性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含糊,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就恨恨而去了。钟会精心结撰了一篇《四本论》,他非常想让当世做论的高手嵇康看看,却又不敢当面请教,于是远远地把文章从窗户扔进嵇康的屋里,转身就跑。钟会如此低声下气,倾心相与,不成想结交不成,反取其辱,当然衔恨在心。他终于得到了一次置对手于死地的机会。
嵇康有一个朋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吕逊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当然不干,打算告官,并与嵇康商量。嵇康却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把吕安按下了。谁知吕逊心里不踏实,反诬吕安“挝母”不孝,打算把弟弟投入牢狱以绝祸根。吕安自然不服,申辩,并引嵇康为证,于是嵇康到案作证。这样一件事,别说处死就是判罪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嵇康竟然就此被判了死刑,因为主理此案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隶校尉钟会。钟会的判词是这样说的:
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仪。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世说新语·雅量》注
就事论事,这个判决是怎么也说不圆的。钟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根本撇开具体事实,而站在“清洁王道”的高度,整个地清算嵇康其人,这样,嵇康当然罪无可逭了。但嵇康毕竟是名士领袖,要杀他非大将军司马昭点头不可。钟会不愧有张良之才,他摸透了司马昭的心思,只轻轻地说了句“康乃卧龙也”就要了嵇康的命。钟会的意思是说,嵇康是诸葛亮一流的人物,一人可当百万兵,既然他不为我所用,将来帮助敌人造起反来,必然遗患无穷,所以必须赶紧杀掉。其实钟会心里清楚得很,嵇康虽然是做论高手,琴艺高手,但这都是些名士伎俩,说到文韬武略、权谋机变还得数他钟会,他只是要嵇康死,所以姑且这么抬举他一下。
以嵇康的“刚肠疾恶”、严气正性,自然不屑向钟会之流鸣冤叫屈、哓哓申辩,那么剩下的路只能是从容就死。《世说新语》说: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而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曲,予靳固不也。《广陵散》于今绝矣。
在死的面前,嵇康仍然风神潇洒。金圣叹式的“砍头大痛也,予以不意得之,不亦快哉”,不免显得大言炎炎,底气不足;阿Q式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的绝望叫嚣,更是伧俗可笑,等而下之。嵇康用他的死,完成了对生命的最后一次审美观照,让人们看到生命和人格的美的光辉。
假如让我给嵇康下一个品题,那么我的品题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狂士。狂得不识时务、不知好歹,其浩然之气,非止“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甚至生死都不能改其节;狂得令钟会之流心虚气短,不能不用他们的卑鄙龌龊以凸现嵇康睥睨一切的人格优越;狂得那么不近情理,却又处处合乎美和人性的本真。然而历史上的狂士往往被目为“异端”“叛逆”,因而遭受迫害,难有好的下场。但历史又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觉醒者、先驱者,他们付出痛苦以至生命的代价,却捍卫了人的尊严,他们的“狂”恰恰是凡庸而污浊社会的最可宝贵的清醒剂、解毒剂甚至催进剂。
后来书读得多一点,对嵇康其人及其时代知道得多一点,最初那点恶感消释了,对嵇康的名士脾气也越来越理解,越来越佩服,现在则简直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发其狂士之高致,不如此不足以标其超迈峻洁之人格,一句话,不如此嵇康就不成其为嵇康了。
鲁迅有一篇名字很长很怪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学史(说是文化史也无不可)随笔。它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胜义叠见,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历史概括力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叹赏不置。在这篇讲演中,鲁迅提出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我大胆地作了进一步的推导:魏晋不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自觉、美的自觉———合而言之,就是对于人的审美的自觉———的时代。
其实,早在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就很盛。不过,那时品评的范围很小,主要集中在道德方面。品评的权柄,操纵在少数长吏及号为人伦之鉴的品评家的手里。到了魏晋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品评人物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而泛及人的所有方面。品评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整个名士阶层的习尚。更重要的是,品评的眼光不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政治的、道德的,而是审美的。魏晋风度,这个极富审美意味的概念,就是对那个发现人的美、欣赏人的美的时代的准确概括。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魏晋多“美人”(不是指美女,而是指美男子),有“面如傅朱”的何晏,有被人“看杀”的卫玠,有一上街便被妇女们“连手萦之”的潘岳,有号为“玉人”的裴楷,有“轩轩如朝霞举”的司马昱,有“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美人之多,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美男子的总和,可以说魏晋是个盛产“美人”的时代。这当然不是因为历史偏爱它,所以让它格外出产美人,这种情况恰恰是由当时流行的审美性的品评人物的风气造成的。
嵇康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门第不高。他的父亲做官只做到太守,死得又早,使他早早成为孤儿,靠母兄抚养长大。他似乎很有志气,通过自身努力,居然早早成名。那是一个名士时代,一成名士就无所不可。凭着少年名士的名头和“龙章凤姿”的品貌(他也是有名的美男子),嵇康得以与魏宗室联姻,娶了魏沛王的女儿长乐亭主。婚后,做了郎中、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但中散大夫并不是什么正经官职,无职无守,也许有一份干俸吧,因此,他得以与阮籍、山涛们结成竹林七贤,在山阳自在逍遥地度着他名士生涯。假使处在太平盛世,他也许会就此名士风流下去吧。然而他处在魏晋改朝换代之际,政治环境极其险恶:一方面司马氏集团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准备迫使曹魏王朝“自觉”禅让;另一方面,曹魏集团不甘被禅代的命运而作最后挣扎。嵇康是魏宗室女婿,因此天然地属于在这场斗争中没落的、必然被取代的曹魏集团,因此也就天然地处在司马氏的政治迫害之下。
当年,曹操就是通过他攫取的权力,迫使汉王朝“自觉”禅让的。而今,司马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其残酷性远远过之。曹操并不怎么杀人,只杀了两个名士。一个是孔融,一个是祢衡,祢衡还是借黄祖之手杀的。这固然是因为曹操雄才大略,懂得爱惜人才;也是因为当时三国鼎立格局未定,需才孔亟,如果不善加笼络而肆行杀戮,无异驱逐人才以资敌。司马氏则奉行赤裸裸的杀人政策,他们杀何晏,杀夏侯玄,一直杀到嵇康,杀了一百多个名士还不肯歇手。或者要说,当时有些名士闹得太不成话,败坏了纲常伦纪,沦为名教罪人,所以要杀杀他们,以挽世风。这是皮相之论。胡闹是名士的特权,也是名士的标记,不胡闹就做不成名士。司马氏在这上面倒是相当优容的。清谈没关系,喝酒、吃药没关系,甚至“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态,同禽兽”也没关系。这都是小节,小节出入可也,但大节不容含糊。什么是大节呢?大节就是政治,就是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的搏斗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这才是司马氏集团为名士们设立的“dead line”(死线),犯者必死。
在这样的政治恐怖下,一种混世保命的哲学在名士当中流行。不过,那时不这么叫,而美其名曰“慎”。李康在他的《家诫》中说,为官之道有三,曰“清、慎、勤”。又说“清、慎、勤”当中,“慎乃至大”,万不得已,“清、勤”可弃,“慎”却决不能丢。“慎”俨然成了最高德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慎”能保命。据说,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昭许他为“天下之至慎者”,所以他保住了性命。又据说,嵇康也是个“慎”者,然而他的“慎”贯彻得不彻底,在最关键的政治抉择上不“慎”了,所以丢了性命。
司马氏并不胡乱杀人,他们只是用杀人的手段,为名士们指示一条出路,告诉他们生之所在,死之所在。面对这样的高压,名士集团很快分化成三派。一派以嵇康为代表,他们不识时务,不知顺逆,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可称为反对派。一派以阮籍为代表,他们明哲保身,与司马氏的关系若即若离、半推半就,可称为中间派。一派以钟会为代表,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甘心为司马氏所用,可称为司马派。让我们先来看中间派,看阮籍。
阮籍可说是那个时代最痛苦的人。嵇康、钟会他们对待司马氏的态度虽然相反,但都心意已决,不再徘徊瞻顾,而阮籍就难过了。他既不愿卖身投靠,又要与司马氏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个中分寸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好在他有“至慎”的法宝,又能装酒糊涂,司马氏想招他为婿,他居然能大醉六十日不醒,使得提亲的人无法开口,只好作罢。然而镇日临深履薄,战战兢兢,其精神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他才会“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方,“辄痛哭而反”;才会“好作啸”,没事经常往苏门山中仰天长啸。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行,其实都是他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痛苦出诗人,作为他“苦闷的象征”的咏怀诗,居然在文学史上放一异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学成就。
嵇康虽然是名士领袖,但在曹魏集团中并不是什么重要脚色,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说到底只是一介名士而已。所以司马氏对他一直采取笼络的态度,所以钟会才会一再要与他结交,山涛才会推荐他做吏部郎。尽管他有些把柄———比如写文章,发怪论,其间不无影射司马氏之处;又比如他曾想起兵响应毋丘俭造反,司马氏也不纠缠计较。然而他却不知好歹,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地、坚决地宣示了他对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这才走上了死路,他曾经得罪过的钟会就是送他上路的人。
钟会出身高贵(他的父亲钟繇官居太傅),成名很早,文武兼资,是司马氏集团的心腹谋士,时人比之为张良。钟会只比嵇康小一岁,凭他的门第、才能、名气,要与嵇康结交,不说是折节下交,至少也不算高攀。但这位仁兄在嵇康面前似乎格外气短,怎么看都像是巴结。一次钟会巴巴地从洛阳跑到山阳,专程拜访嵇康。其时,嵇康正与向秀在树下锻铁,看也不看他一眼,话也懒得跟他说一句,只是在他要走的时候才挑衅性地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含糊,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就恨恨而去了。钟会精心结撰了一篇《四本论》,他非常想让当世做论的高手嵇康看看,却又不敢当面请教,于是远远地把文章从窗户扔进嵇康的屋里,转身就跑。钟会如此低声下气,倾心相与,不成想结交不成,反取其辱,当然衔恨在心。他终于得到了一次置对手于死地的机会。
嵇康有一个朋友叫吕安。吕安的哥哥吕逊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当然不干,打算告官,并与嵇康商量。嵇康却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把吕安按下了。谁知吕逊心里不踏实,反诬吕安“挝母”不孝,打算把弟弟投入牢狱以绝祸根。吕安自然不服,申辩,并引嵇康为证,于是嵇康到案作证。这样一件事,别说处死就是判罪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嵇康竟然就此被判了死刑,因为主理此案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隶校尉钟会。钟会的判词是这样说的:
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仪。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世说新语·雅量》注
就事论事,这个判决是怎么也说不圆的。钟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根本撇开具体事实,而站在“清洁王道”的高度,整个地清算嵇康其人,这样,嵇康当然罪无可逭了。但嵇康毕竟是名士领袖,要杀他非大将军司马昭点头不可。钟会不愧有张良之才,他摸透了司马昭的心思,只轻轻地说了句“康乃卧龙也”就要了嵇康的命。钟会的意思是说,嵇康是诸葛亮一流的人物,一人可当百万兵,既然他不为我所用,将来帮助敌人造起反来,必然遗患无穷,所以必须赶紧杀掉。其实钟会心里清楚得很,嵇康虽然是做论高手,琴艺高手,但这都是些名士伎俩,说到文韬武略、权谋机变还得数他钟会,他只是要嵇康死,所以姑且这么抬举他一下。
以嵇康的“刚肠疾恶”、严气正性,自然不屑向钟会之流鸣冤叫屈、哓哓申辩,那么剩下的路只能是从容就死。《世说新语》说: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而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曲,予靳固不也。《广陵散》于今绝矣。
在死的面前,嵇康仍然风神潇洒。金圣叹式的“砍头大痛也,予以不意得之,不亦快哉”,不免显得大言炎炎,底气不足;阿Q式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的绝望叫嚣,更是伧俗可笑,等而下之。嵇康用他的死,完成了对生命的最后一次审美观照,让人们看到生命和人格的美的光辉。
假如让我给嵇康下一个品题,那么我的品题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狂士。狂得不识时务、不知好歹,其浩然之气,非止“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甚至生死都不能改其节;狂得令钟会之流心虚气短,不能不用他们的卑鄙龌龊以凸现嵇康睥睨一切的人格优越;狂得那么不近情理,却又处处合乎美和人性的本真。然而历史上的狂士往往被目为“异端”“叛逆”,因而遭受迫害,难有好的下场。但历史又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觉醒者、先驱者,他们付出痛苦以至生命的代价,却捍卫了人的尊严,他们的“狂”恰恰是凡庸而污浊社会的最可宝贵的清醒剂、解毒剂甚至催进剂。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