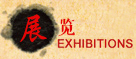当天才泄露太多秘密时,上帝就会收走他的生命,无疑,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位天才。
即便是鲁迅,也拥有了56年的世俗肉身,而王小波,以45岁的英年早逝,并且,发表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大障碍,可见他是个连上帝都嫉妒开口的人。他那毫无避讳、汪洋恣肆的滔滔言说,是那样巧妙地兼备了神性和人间性,倾倒和折服了众多读者、研究者,而这些受众又是那样的参差多态。
当王小波的遗物手稿以图文并茂、具像可视的形式办成展览时,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变得更加生动和完整。2005年4月11日至5月13日,在王小波去世的八周年祭日里,北京鲁迅博物馆筹备了这样的展览,并多次邀请其亲友、学者、编辑、网民到会做漫谈,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为当代作家举办的展览。有关王小波生前身后的星星点点在这里像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掀起参与者心中的层层涟漪,更为王小波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体验。
一
王小波仿佛是块天然的璞玉,短暂地发光于人世间,当有人偶然发现,欲拿起刻刀近前雕刻时,上帝马上就把它收走了。他的与众不同与他的平实朴素,他的嬉笑怒骂与他的认真严肃,他的玩世不恭与他真诚地拥抱生活,他不按常规出牌,却又如此尊重人性的规律,他清晰冷静的理性与顽皮放纵的狂热,他逻辑推理的审慎与横溢诗情的浪漫,他站在边缘的特立独行与中心磁石般的亲和力……这一切看似水火不容的对立元素,在王小波那里却是浑然一体且又摇曳多姿的。
当王小波式思维在我们面前呈出现来时,完全体现为一种属于自我的设计。它以不断自我否定,和随时保持自省的姿态向世界敞开:他热爱文学,便质问文学:是道德法庭的判决,还是人性演出的舞台?他是一个作家,便质问作家,对自己胜利了吗?通过写作改变自己了吗?他研究西方学术思想,他质疑西方学术思想的有限性;他是中国人,他质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是知识分子,他质疑知识分子的虚妄;他是男人,他质疑男权思想;乃至他是人,他也质疑人不可思议的天性……。总之,对于任何看起来理所当然、不可质疑的事情,王小波都要加以怀疑,这不仅限于外部权威,更没有排除人类自身,这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体现。
王小波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不断地质询中披露了某种思维方式的荒唐可笑,尤其是那些滋长在自己的本土中国的思维方式。如果用他极富个性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总是寻找所谓神奇的诀窍,以期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不弄明白真相,便瞎积极振奋;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顺嘴就圣化自己;拿道德来评说艺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用知识权力来统一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培养人人自我设计的能力;以愚蠢教人,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对于物质贫困,宁肯消极忍耐,也不提倡动脑子;面对科学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不允许幽默,只允许假正经;不能理解随机事件,脑子里只有天经地义;感情随时表演给人看,把肉麻当有趣,当成美,瞎浪漫;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道、钳制思想、灌输善良;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把生活变成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
对于需要思想,就如同需要空气和水一样的王小波来说,生存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斥着狂信和非理性思维的社会里,注定什么也收获不到。为此,他写下脍炙人口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文,最典型地体现了他那不断打开,自行创造的不凡追求。他写道:“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如此敢于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的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1]
王小波的随意和洒脱,就这样成为反抗上述思维弊端的最好诠释,同时一点也不显得刻意追逐另类。这决不是一个以破坏文化为乐的无厘头的姿态,这是一个珍爱自己精神家园的守护者的宣言,他的内心深处生长的是智慧和真性的情感,涌动着不息的诗意的溪流。
人文事业之于王小波,是宁静童心视域下的这样一条路:“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2]为此,王小波要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他厌恶模式化的生活,认为生活的支点是我们自己,一个社会的思想群落应该是参差多态的;他爱一切人类想出来的有趣、飞扬的东西,爱自己凝结、坚实的思想,爱迷人的美;他渴望平等的友爱,狂怒于平庸生活,不甘没落;他认为不断地学习和追求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他对知识的向往是一种完全纯美的境界,他非常怀念一位普通的数学老师,深刻铭记他的这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并由衷地赞叹“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使我终生佩服。”[3]显而易见,王小波所谓的“精神家园”,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俯瞰高度,和超凡脱俗的崇高信念,更不是高度抽象化的浪漫叙述,而是朝向开放的未知领域的永恒追索,是把一件美好的东西创造出来时的快乐体验,是心灵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不可抑制的渴望和冲动。
尽管如此,王小波从不自认为自己的思想能够代表自由和公共的声音,从不自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最好的,值得别人效仿。为此,他决不故做惊人之语,正像他决不故作天真一样。对于他身后所掀起的种种热潮,很大程度上是读者的主动呼应,他本人甚至永远不知道,大概也从来没有期待过。
王小波自主质疑的思维方式在思想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应该代表智慧的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认识不到上述思维方式的弊端,甚至更加被其束缚。比普通人更为有害的是,他们使命感太强,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以致于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有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的救世情结,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4]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用佛学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的“我执”太严重了,总是不肯脱下那件旧长袍。结果,他们将那些自以为是的思想繁殖成迷宫般的话语圈,一手筑就了声名狼藉的疯人院,乃至是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就拿“国学”来说,对知识分子而言,它的“制高点”是一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5]对此,王小波是非常警醒的,“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6]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受虐倾向,因而成为权力的柔顺剂,而不是解毒剂。王小波小说里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红拂夜奔》里的李靖、《未来世界》,《2015》里的我舅舅,当强大的权力机器话语不再施暴,他们的科学或艺术生命力也同时完结。
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现在看来是非常深刻的,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怀疑精神多么高明,在他看来,这只不过起源于饥饿的肚肠罢了,而“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7] 这就是说,有时候知识越多的人,思惑反而越重,束缚也越大。看似自己能够做主,其实只是做思想的奴隶。在王小波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糊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就会变得心明眼亮。在《积极的结论》中,他写到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很多科学家还积极为之论证,而他的姥姥,一位农村老太太,听说后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事实证明,没有比这位没文化的老人更明白事理的了,这只是最简单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眼中的理性没有多么高深玄妙,就是指的这种清醒的头脑。他的杂文经常这样直接参与到生活中,提醒那些制造虚妄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不要忘记这些思想产生的直接基础和来源,使他们从凌空的高蹈中,能够经常感受坚实的大地,重新认识生命的本来。
那么,对于王小波来说,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角色呢?“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8]如果不幸生存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就应该保持沉默,这就等于是守护了自己的理性。并且,“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9]可见,王小波所不断强调的,是智慧、创造、思维的乐趣,是来自知识自身公正的游戏规则,这看似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象牙塔内的理想,仿佛是接受了权力的放逐,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和阐释者的角色[10],甚至放弃了作为“有机知识分子”[11]的可能,但我认为,这仅是相对于文化荒蛮状况而言的,是因为知识分子曾经太关注道德,而根本就没有真正思维过,没有真正体味过知识所带来的智慧和美的境界,而只是热衷于急功近利地用意识形态化的表面知识去教化民众。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因为他们太爱讲理,依赖讲理来生存,而根本不是依赖知识本身应有的境界。而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所以,非常戏剧化的是,社会往往并没有变得更富于这类知识分子所设计的那种人性,恰恰相反,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眼中的“被启蒙者”在规划并实施着社会秩序,并且与自认为是“启蒙者”的他们之间早已撕破联合。这是非常惹人深思的一份来自王小波的思想遗产。
二
像不甘于被别人设置生活一样,一个时刻葆有自主质疑思维方式的作家的创作也绝对不会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去追踪和反映现实。他眼中的文学想象力必然同样是独立自主,自己取得意义的。
对于王小波来说,在思想领域内同专制主义权威论辩是徒劳的,因为一论辩就会陷入其专制的语义,因此,转变权威语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种说法。王小波就是这样为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份崭新的审美经验,他以飞翔的文字证明:一个故事为什么非要从头讲起?从任何一个缺口讲起的为什么不能是同一个故事?为什么在用第一人称讲述一个故事时,不能忽然变成第二人称?小说为什么非要描述而不能插入逻辑论证的声音?性为什么不能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不能成为对庄严事物的比喻呢?
不可否认的是,王小波的早期作品《地久天长》等仍然是一种再现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战福》、《猫》很有鲁迅的阴暗色调,人性恶被描绘地触目惊心,读后的感觉沉甸甸的,并不像他后来的作品那样可以让人笑出声来,同时又鼻子发酸。事情发生转折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其时,王小波正在美国留学,并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后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唐人秘传故事》。当国内最先锋的审美感觉还停留在西方现代派时,王小波的作品里已经出现了拼贴、戏仿、反讽、滑稽这些后现代的美学元素。他在小说叙事中,不断进行自为的建构,以极富个性化和寓言化的叙事穿行于古今中外,对原有启蒙性宏伟叙事予以解构。标志其创作高度的《时代三部曲》中的《青铜时代》即基本脱胎于这些仿古小说的先锋实验。为了摆脱人性中所受到的沉重奴役,进入创作成熟期的王小波更大量地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逻辑和面目一新的检验方式来认知世界,驾驭语言,并从中找到了最适合表现他内心思想的文学符号,那就是性。按照传统观念来看,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有生存上的负疚感,而在王小波的笔下,性道德的述词不再是善或恶、符合还是不符合习传的道德标准,而完全是个人身体感觉的自主表达。那些想象中的人物,无论是陈清扬、红拂还是无双,都一度是自为性的个体存在,依自如道德生活的个人。不过,这种自如又必须仰赖于传统道德视角的无处不在,陈清扬与王二,红拂与李靖都是在道德权威的逼视下才得以达到完全自由的性爱境界。
但是,如果就此把王小波的小说看作是清除流俗的文本,那就一叶障目,看不到更多的迷人风景了。实际上王小波丝毫不热衷于两性性行为的渲染和铺陈,他领悟到由性而波及到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叙述人才可以毫无束缚地穿行于古今时空,出入于人物的心灵内外。在他那里,性既可以是一个经常被拿来做调侃的日常话题,也可以是完全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的人生境界,既可以是一个有关权力等等内蕴丰厚的隐喻,也可以是一个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范畴,既可以是一个游戏,也可以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通过性这一载体,小说在王小波的手中实现了自主性。他用高超的叙事策略,做到了可以不用悲剧色彩而流泪,不用喜剧色彩而狂笑。小说经常使用一些逻辑论文常用的推断词语,诸如“这说明”、“众所周知”、“如前所述”、“事实上”、“关于……的事后来是这样的”等等,这些以“缺场”者的口吻和叙述人的语调插入的判断和总结性文字,终止了以往小说竭尽描述之能事的惯例,反而出其不意地从不同叙述视点廓清了故事的脉络,出现了故事表层叙事与深层意蕴始终在对话的美学效果。尤其是《万寿寺》,完全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亦即元小说[12],关于薛嵩的故事不断地重新开始,每一次开始都是其他无数开始的回声,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地进行特殊的对话和交流。当然,所有的对话和交流中都贯穿着性这一符号。当主人公恢复了记忆,“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我们仿佛看到叙述者是多么不情愿走出审美世界。他甚至把隐喻、象征、意味等等美学元素看成是负累,充满个人气质的想象力完全是在为了小说而小说地尽情挥洒。小说的自主性甚至是作者难以控制的,这无疑反映了文学自我意识的高度发展。
对于那些初次接触王小波的人来说,上述叙述风格完全超出了他们在现实主义传统内所形成的阅读期待,仿佛是王小波长有一双神奇的翅膀,给他们带来了飞翔的感觉。实际上,王小波只是像希腊神话中的柏修斯那样穿上了长有翅膀的鞋子而已。他换一种说法的语言颠覆、叙述革命、解构翻新,并不是凭空创造,都可追其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创作踪迹,他的幽默的亵神显然是继承了拉伯雷、托马斯·曼,直至昆德拉;他文本中的人生韵律来自杜拉斯,他的恣意驰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来自卡尔维诺;他的繁复与狂欢是巴赫金的;他的以施虐/受虐模式揭破历史的秘密与权力运作的游戏规则是福柯的……这样说,并不在贬损王小波的创造性,恰恰相反,一个善于吸收异域营养的人是最聪明的小说家,更何况他匠心独运地将其镶嵌于中国特有的疯狂的政治语境中,用诗一般极富质感的汉语讲述出来。在他营造的超然世界里,语言已化为飘逸的云朵,流动的尘埃,尽管它们背后指涉的社会性话题曾经是那样的沉重,但他并没有随意地,漫不经心地使用语言,他甚至是非常挑剔,乃至是为之呕血的,历经十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就前前后后被修改过几十遍。
王小波所带来的全新的审美经验与他那高超的叙事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犹能看出些启蒙色彩,那么他的小说中则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图,他甚至是无心地沉醉在那种反专制,反人性的故事中。王小波没有鲁迅那代人启蒙心态的焦灼,他写作时的身心是完全放松的。诗与思结合的言说,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叙事思想家。王小波在拓宽读者审美视野,丰富其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意欲穷尽中外文学可能性的非凡创造力和表现力。几乎每个与王小波相遇的读者都在惊叹,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可见他的小说怎样以惊艳的效果攥住了读者的心。不仅如此,他以新的审美形式冲击着社会道德问题,改变着人们打量世界的方式,从而得以重构历史。
三
艾柯说:“为了不致给通往文本的道路制造麻烦,作者最好在他完成写作时立刻死去。”[13]巧合的是,王小波真的故去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死后出版的,理论的夸张就这样被冷酷的现实所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死恰好解放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当王小波的意义被充分意识到时,占统治地位的共同期待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此之前,其意义一直是隐而不彰的。王小波在中心文坛的迟到,显示了中国主流评论界对某种新思维方式的一再拒绝,但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伟大的作品总是写给未来的,正是时间距离导致了理解的过滤,而更多的读者却因此成为历史文本的知音。
正是王小波把文本与读者的传统距离,变成了读者同作者的意外邂逅。由他身上而体现出来的人间性,不仅指作品中的人间关怀,更主要的是他从来不自说自话,而是比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地重视和尊重读者。他平心静气地和读者交流,“引导”这样的词语从未在他的艺术思维当中停留过,因而,读者也尊重他。他吸引的全是与他有着心灵共鸣的读者群。他曾经说,自己只需要二三万的读者,真正理解他的有这些就够了。如果说鲁迅还在质疑启蒙的有限性,那么王小波直接就抛弃了这个字眼儿,他甚至认为读者是不需要引导的,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没必要用文学来引导,因文学而走到一起的人,本身就是互相慰藉的,如果存在启蒙也是相互的,他“永远不会想到把别人的灵魂据为己有,只希望灵魂互通”。但恰恰是没有刻意思考这一中国新文学百年主流命题的王小波提出了启蒙的本质,那就是自主的、质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对他来说会带来无穷的快乐,一种永远不会让人感到肉麻的快乐。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他写道:“前几年,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这说明,王小波是把自己放在和读者平等交流的位置上的,当然,他意中的读者群是那些能用自己的智慧明辨是非的人,既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并不自认为是精英。对他来说,他们是他渴望诉诸的故乡人,而不是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的异乡人。
理解了王小波的人间性,似乎就会对其死后被媒体成功的炒作成都市文化消费现象不再只是愤愤不平,从王小波逝世之日起,网上就不断地掀起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火热追捧乃至摹仿其写作的门下走狗联盟,从此拥有了一大批拥趸者,这显示了王小波的严肃艺术取向向下拉平成流行文化符号的大众性。如果说消费社会的商品逻辑部分遮蔽和扭曲了王小波的存在意义,那么八年后,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这样的公益机构举办的第一次当代作家的展览上,那些完全没有功利色彩极富深情的观众留言,充分证明了王小波在众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其神性在人间的真实投影,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发自肺腑的感恩之声和失去亲人般依恋的呢喃:
感谢王小波,能帮助我保留一丝飞离泥泞的念头,偶尔还能努力挣扎一下。
感谢您用您的自由精神点醒了我,让我重新思索:生活是什么?而我又该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感谢他让我思考了“智慧”这个美丽的词语,鼓励我思考,我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感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知道生活还可以有趣的。虽然身边的一切还是那么滞重,但有你的文字在身边,我已能够从容面对。
……
除此之外,大部分观众都在赞美王小波,称他是真正活过的人;从具体的可感的生活中,洞见智慧和美感;当代最杰出的汉语、最杰出的思想者。开辟了一种言说与批判的维度,一大批人因之而学会了思考。王小波的肩膀上长着他自己的脑袋。没有他,我们摸象的步子可能还会更慢。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还是一样会让看他作品的人大吃一惊进而肃然起敬。他使时代加重了色泽,使我们的目光变得透彻。他在五线谱上留下的歌曲将会被传唱下去;在我们前行的行列里,永远有他的身影。甚至声称《我的精神家园》是自己的精神教父,时常觉得王小波没有死,就在自己的血液中。最重要的是,他用文字告诉了读到他文字的人思维、有趣、智慧、美……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更有人表示,决心像王小波那样,用生命去做自己,走到海边的幽冥中仍能回复到对生的信念和探索……
使我惊奇的是,王小波的忠实读者中还有不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大的一位都八十多岁了,他们对小波的喜爱与狂热丝毫不亚于年轻人。这说明,当王小波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颠覆了那些束缚我们的常规理念时,任何一位深受其苦的人都会感觉到好像于漫漫暗夜中看到了迟来的光,这个时候,只要是目力可及的人,都是同道,年龄、职业、阶层都已不成问题。正是王小波独特的思与言构成的存在之家,烛照了众多追随者曾经晦暗的内心世界,他们怀着对彼岸世界完善和永恒的追索,渴望成为这一家园中人。
四
佛说人间一切皆梦幻泡影,那么王小波追逐的这个幻象也许因显得智慧、高尚,和彼岸的遥远,便更容易被大众所尊崇。所谓自由、美好、意义仿佛使王小波独特的个人话语仍然成为时代话语的独特表达式,或者说是知青部落的独特表达式。作为一个从话语疯狂膨胀的知青时代走过来的作家,王小波的发声显露出的仍像是一代人的群体姿态,因为对于八十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而言,这些词汇岂但不陌生,简直曾经纷纷争抢着以此搭建自己的言说途经,但是仔细分析一下,王小波又有所不同,即便创作起步时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类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所迷恋的仍主要是以诗的想像超越现实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确定归属,他感到唯有此,人才会忘却世俗的烦恼和痛苦,变得轻逸而超脱,这对陷溺于尘世的泥淖中人是富有极大吸引力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这种境界不是只有思维和学习才能够获得,也不是只停留在美和有趣的层次,它甚至不是永恒的,而是转瞬即逝,需要不断把握的。任何个体在生存的分分秒秒中,其实都会体验到这种快乐,顿悟生命的真谛,比方说,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时;农民辛勤耕种获得丰收时;甚至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最后恢复野性时……在他们的生命痕迹中肯定都会有那么一刹那会忘却尘世烦恼,感受到无比开朗的生命境界。但是,王小波却认为“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14]这样说,就不免会让很多普通大众感到难以企及了。因此,在我看来,王小波之所以如此珍视这种他所谓的思想自由境界,不可能仅是神思存在的天命召唤,当另有世俗原因。作为以思考为业的求知者,给他带来上述珍视和追求快感的,不是别的,正是曾经严酷禁锢他的社会文化环境。假如在一个稍加自由的国度里,他也许就体会不到这种追求和呼唤的强烈快感了。学者丁东谈到王小波的小说幽默、荒诞、有趣,充满了智性,这种风格到现在仍然得到人们喜爱。这说明生活中荒诞的东西太多,人们能够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与荒诞保持平衡的力量。然而,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情节还要更加荒诞,由此他讲到王小波曾质疑他们去贫困地区发传单的行为,而实际上这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可见王小波的思维预设里早已埋伏下种种政治话语的哨卡,他随时准备着出击和讽刺,还有黑色幽默,连他自己都说“我不爱看色情书,但我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15]是极权社会的所谓思想禁锢给了他这种期待心理,他为此而逆反、甚至臆想了,假如真是这样,他已成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成为知识分子受虐倾向中的一员。当然,一次漫谈会上的回忆不可能在此作为推断作家创作心理的证据,但这至少可以与阅读中朦胧的感觉相印合,不可否认的是,王小波面对极权社会的压抑是兴奋的,可以说这成为他大脑中永远的兴奋灶。
在王小波那里,生活愈沉重,想像力愈飞驰,他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一文里这样写道:“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 正是这种种积重难返的障碍成为他编织小说的内在冲动。在《关于格调》一文中,他又说:“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质……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这就透露出了王小波的部分文学观,一方面,他为什么要写作,“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16]另一方面“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刚的世界。”[17]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汲汲追求的超现实的理想状态,那么,后者就可以说是他以文学来实现知识分子参与文化解构和建构事业的实际宣言,这是文学在他眼里存在的部分理由,更或者是他以文学而存在的部分理由。
由王小波的创作动机带来的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性是一种开放、宽容、理性的精神态度,而中国的现代性总是在非常态的思想语境下作为一种应激反应催生出来,然后便偃旗息鼓,似乎在等待下一次非常态事件的重新刺激。换言之,一离开专制的环境,知识分子就仿佛失去了理性反思的能力,假如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那么它不能不说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它始终不像是自然发育成熟,并会更自然地生长下去的样子。没有严酷的文革就没有王小波,就像没有封建社会的没落就没有鲁迅一样。他那些特立独行的思维诞生于文革中人性的高度压抑和思维的狂信状态下,假如在略微人性正常的社会形态中发育,中国还会诞生王小波式的现代英雄吗?反过来说,王小波的忠实读者,他们的心态是不是总停留在特殊年代,被某些挥之不去的东西所缠绕呢?知青喜欢王小波是因为他们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70年代生人喜欢王小波是因为这里曾有他们成长的精神资源;而80年代生人喜欢王小波则是因为文革早已进入了审美距离,而这一切统统源于中国那个“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特殊时期所给人带来的种种超乎寻常的想像和刺激。而在当下物欲横流,看似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强大的权力机器话语不再构成尖锐的对立面,当专制和人性的奴役隐匿成另一种面目出现时,我们又该何为?
由此我想,王小波现象会不会是中国式现代性的一个幻觉?所谓幻觉不是不承认王小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而是说他所代表的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是不是很短暂就消失了?甚至只是一种烟火花影?它没有真正扎根,更不能奢望它之后的生命力。因为由他而拓展开来的自由视界,最初延续的是80年代面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政治反思的思维,因而构成了一种被更隐秘地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身份的想象,后来又在都市文化大行其道的市场体制下,被物化为逃离体制的体现和行动,最后则被弥漫和歪曲成一种时尚的生活态度。这种与诞生在中国近现代乃至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日见高涨的道德禁欲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联的现代性,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慰的现代性。作为一名在现代性追求之路上的匆匆过客,王小波“生前寂寞,死后哀荣”的文学遭遇已经成为明证。
不仅如此,王小波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都是一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追索,因为只有这样的知识、美和思维才能给他带来澄明和敞亮,才能完全摆脱外物和他人的羁绊,达到直接聆听神祗心声的人神对话的境界,但是,这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幻觉,无他,中国的文化蛮荒状态曾经太严重了而已。让我们冷静的想一下,是王小波给我们带来的审美经验太丰富,还是我们自身的审美经验太贫乏?如果你读过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也许你就不会如此振奋了。只有当王小波的神圣性被消解了,不再构成轰动效应,而成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话题,我们的现代性也许才具备一点常态。
注释:
[1]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2]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3] 王小波:《跳出手掌心》,《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4] [8] 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33页。
[5][6]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第41页。
[7]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9]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0]关于立法者和阐释者的角色隐喻,齐格蒙.鲍曼认为,前者是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后者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目的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具体可参见齐格蒙.鲍曼 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 “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出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主所创造的,比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葛兰西相信有机的知识分子能够主动参与社会,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
[12] 所谓元小说(metafiction)就是以小说为对象的小说,也有学者把它称为自我意识的小说或自我反思的小说……元小说的作者通常总是一方面进行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又在小说中对这种创作行为加以评论、展示小说的叙述成规和创作过程,把小说创作的人为性、虚构性充分地揭示出来。
[13] 罗钢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4] 王小波:《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15] 王小波:《文明与反讽》,《沉默的大多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