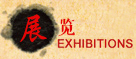鲁迅与日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早年他到日本留学,从那里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也是在那里开始文艺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此后,他与日本人民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对日本民族认真、善于学习等特点是很欣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宽容的,后者甚至点燃了其日后弃医从文,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终生理想。
早在仙台医专时,鲁迅就在时事幻灯片里目睹了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杀害俘虏的残酷景象,这使他深受刺激:被杀害的是替俄国人作侦探的自己的同胞,围观的竟也是自己的同胞,而教室里的同学们更是热烈地鉴赏着这有趣的场面,不时地拍掌欢呼!这对立志学医的鲁迅来说,是个空前的打击,他忽然感到国民的体格再健壮也是没有用的,倘若不改变他们的精神,将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永远受到外族欺凌。从此,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伟业,提倡文艺运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由觊觎中国到步步入侵,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在自己的领域不遗余力地开展救亡运动,这种救亡以其特有的启蒙基调展现出来,渗透着“民族魂”的深沉忧患,然而,鲁迅的用心良苦和超越时代拘囿的勇气却总是被庸人误解,“汉奸”的骂名甚至直到今天仍可在互联网上时有所见。
这样的误解基本上是指责鲁迅当时的言论过于暴露黑暗,太悲观消极,起不到鼓舞民心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肤浅的急功近利的救亡论者,他始终把国家民族的沦亡与民众精神的沦亡相联系,把以笔为旗的救亡行动与国民批判,尤其是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批判相联系。
试看,面对强敌的入侵,我们的国民政府是如何表现的呢?
1931年9月,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上海等地的爱国学生,多次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愿示威,强烈要求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的疯狂射击,珍珠桥边血流满地。血腥暴行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竟然发了一个电文,说学生们破坏社会秩序,叫嚷什么“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激愤中的鲁迅挥笔写就著名的《“友邦惊诧”论》,怒不可遏地喝道:“好个‘友邦人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这极其精粹的短句,概括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大量事实,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友邦”,实际上是出卖祖国的国民党政府的“友邦”,对广大人民来说,却是死敌。
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并行抨击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匕首与投枪。《漫与》记道:“‘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预设的宝座。”因此,所谓“壤外必先安内”,其实质不过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直截一些,就是“外就是内,本无可攘”了。鲁迅对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汉奸哲学分析得鞭辟入里,把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昏庸腐败的政府不能依靠,国民又是如何争气的呢?鲁迅痛心疾首地发现,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麻木卑怯的庸众,就是投机做戏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当日军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但是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对此种儿戏般的救国行为,鲁迅有形象的描绘:
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二心集》)
除此之外,《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宣传与做戏》、《真假堂·吉诃德》等杂文都是痛斥这些无异于沙上建塔,只能聊以自欺的救国行径,这与国与民没有任何帮助,徒增悲哀罢了。
“九·一八”的炮火刚刚停歇,上海又燃起了熊熊战火。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鲁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公寓,正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这天晚上,一颗子弹突然呼啸着穿过桌前窗户,把写字台后面他时常坐的一把椅子打穿了。幸好那天鲁迅没有写作,否则正中他的胸膛。“飞丸入室”打破了鲁迅平静的生活,转瞬间,他与家人陷入闸北火线,眼见中国人纷纷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自己也不得不避入英租界。后来,等到日本兵不打了,鲁迅就搬了回去,不想,有一天形势又忽地紧张起来,原来,那天是月蚀,按照中国旧俗,老百姓哔哔剥剥地放起鞭炮来,结果引起日本人的恐慌,以为是在开枪反抗。这种现实真是让人感到无奈和荒诞,鲁迅叹道:“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因此,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时,谈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并没有照惯常思路去开口大骂日本,而是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
鲁迅这样讲一点都不过分,就在“一·二八”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的马路上竟然到处都在卖《推背图》;1934年,“华北华南同濒危急”,上海又流传发售“科学灵乩图”,可以问试卷、奖券、亡魂,并声称是“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一时间,社会上沉滓泛起,封建迷信大行其道。面对这样令人失望的政府和愚昧的民众,有人把灾难中的国家寄希望于大学生,并指责北平的大学生不赴难抗日。鲁迅向来不主张盲目的爱国,国难当头,他坚决主张大学生们应该逃难,而不是“赴难”,他认为大学生的本职就是学习,既没有组织,有没有经过训练,也没听说前线的军人缺少,上级下令召集,为什么要去充当无谓的炮灰呢?况且——
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的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
这一切都是国民党一贯“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来“教育”学生的结果。“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不过,鲁迅也没有单方面将责任归咎于国家教育,而同时提醒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论‘赴难’和‘逃难’·南腔北调集》)
不仅如此,鲁迅更是关注儿童的身心是否能健康成长。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鲁迅爱子周海婴在外面玩耍时,竟被同胞当成是日本孩子而挨打。这引起了鲁迅的反思,他觉得中国人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但奇怪的是,鲁迅曾在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给海婴照过相,满脸顽皮,确实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穿着同样的衣服,却很拘谨、驯良,是个地道的中国孩子。由此,鲁迅认为问题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照相师身上,照相师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不同,自认为捕捉的孩子的表情也不同。说到底,还是我们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导致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且介亭杂文》)中国思维教育下长大的孩子,总是低眉顺眼,很“乖”的样子,其实是不敢反抗,少有血性,而民族的积弱之深正缘于此。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鲁迅在五四时期就时常思考的启蒙主题,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救亡运动中,成为中华民族最敏锐和最冷静的神经。鲁迅一再提醒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不难想像,一个值得学习的民族成为自己民族的侵略者,这对“绝望中抗战”的鲁迅来说,其所掀起的内心痛苦比那些盲目狭隘的爱国者要深沉复杂的多。
反过来说,日本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呢?日本对于中国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人自己,甚至当时国人用的本国地图都是日本绘制的最详细,具体到中国每一个村庄的每一口井。“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也曾出现一股日本研究热,但除了一些站在狭隘的、赌气式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散布的低能言论外,稍为有点内容的,却都是从日本人对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剽窃过来的。针对这一现象,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集外集拾遗补编》,说道: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照前例,那时就改称‘英夷’,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也可以注意些现在好像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德、奥、匈、比……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在一片反日抗日的时代浪潮中大声疾呼要向日本学习,这样做,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气,也会冒着被辱骂的危险的,但鲁迅能够穿越时代,看到救亡之根本,那就是国民的愚昧懦弱招致了外敌的入侵,而作为一个不可能上前线冲锋陷阵,而是在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作家鲁迅来说,这应该是我们应该佩服的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实际上,鲁迅时刻在警惕日本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演变,学习固然是一个方面,亲善却是决不可能的。鲁迅预感到日本占领中国后,一定会致力于对中华民族治心的,后来的事实也果然不出所料。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日本帝国主义高唱什么“王道仁政”,鼓吹所谓“日中亲善,经济提携”。尽管鲁迅本人为发展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友好就毫无基础。因此,在同一位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鲁迅把这层意思说的很透彻: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的玩着。(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载《鲁迅先生纪念集》)
无论鲁迅同日本友人的情谊如何深厚,也不论鲁迅怎样客观地批判本民族的劣根性,号召向敌人学习,一旦涉及到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原则问题,鲁迅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他坚守民族气节,以实际行动进行不卑不亢地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和日本友人的赞誉。
为使抗战宣传深入群众,鲁迅曾主编时事和文艺的普及性小型报刊《十字街头》;“一·二八”事变后,他和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当从东北救亡前线回来的青年萧红、萧军出版了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却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难以公开销售时,鲁迅毅然为之作序;1936年,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北平文化界也发表宣言,鲁迅特别注意与之决裂的弟弟周作人有没有在上面签名。就在他临终前几天,还对周建人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希望周作人“不可过于后退”,应该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有所作为。可惜周作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终于成了民族的罪人。
在国际交往的场合中,鲁迅更是严峻地表达过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感情。1935年10月,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访问印度经过上海,通过内山完造求见鲁迅。不曾想,会见过程中,他竟以殖民主义者自居,公然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问题:“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对于这种猖狂的挑衅,鲁迅从容而机智地微笑说:“这是个感情问题吧!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是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驳得野口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载1957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
作为一个“荷戟独彷徨”的自由知识分子,真正使鲁迅看到光明,心灵得到慰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当红军长征胜利时,鲁迅发去了祝贺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中央也评价鲁迅是革命的硬骨头,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了解到陕北生活艰苦,曾特地买了两只火腿,通过地下交通站带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张闻天、周恩来致信冯雪峰,转述了对鲁迅的问候、关切、敬重和信任之情,肯定了其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正是从这里,鲁迅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存在,并从中找到了与自己的思想合榫的地方。他于1936年8月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明确表示: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下,鲁迅对于左翼作家和其他作家也寄予了殷切希望: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6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人,代表当时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行自由宣言》,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初步形成。可惜的是,就在此后不久,鲁迅即因过度劳累,致使肺病恶化而与世长辞。他有幸没有目睹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令人遗憾地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