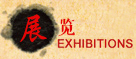咏史诗,即以各类历史因素(人物、事件、场景)为引子和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咏叹、感悟、议论等主观阐释方式,着重展开作者对于历史的主观反映态度的历史诗歌。一般语言精粹且篇幅较短,其主观态度从总体来说也更趋于冷静克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近客观化”特征。
一、咏史诗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背景
相对于中国古典历史传说叙事诗而言,中国古代的咏史诗表现出了更为浓郁的文人气质,从一开始就与文人的个体化文史创作活动密切相关。汉代国力昌盛,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经历了大规模的重建再造过程,在汉代统治者的默许放任下,大批文人主动地投身到非功利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这就为中国古代咏史诗的酝酿萌芽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基础。而我国现存最早的咏史诗亦出自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之手,这首最早的文人咏史诗质木无文,叙议相杂,与更早出现的历史传说叙事诗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且带有相当浓厚的散体史传、史赞残余色彩,在艺术上还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古代文人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来抒发个体自我对于历史的主观咏叹,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人个体主观历史观念的正式确立,对日后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影响弥深。
魏晋南北朝是咏史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文学自觉”、“个性解放”的整体文化氛围之下,文学与史学各自走向分立,追求主体感悟的玄学也逐渐兴盛起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在这种社会思潮的侵染下群体觉醒爆发,这种崇尚心灵自由与自我思考的历史大环境给了以主观阐释见长的咏史诗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熟完善并走向了最高峰。这一时期涌现出曹操、王粲、阮瑀、曹植、张华、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沈约、何逊、萧统、庾信等一大批优秀的咏史诗人,他们的咏史诗作普遍情思兼备、蕴藉深厚,具有先天而来、感人肺腑的诗歌个性和感染力,从一问世就达到了艺术成就的巅峰,呈现出群星璀璨的辉煌局面,为后世的咏史诗歌所难以企及。从这一时期开始,咏史诗的独立诗歌地位和诗歌属性得到确认,咏史诗创作的三种基本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中国文人以诗歌咏叹历史的传统就此开始。
唐代诗歌繁荣,整体诗歌成就登峰造极,但诗人们的关注视点大都集中于现世生活,相对忽略了历史的反思和回味,因此和魏晋时期相比,唐代咏史诗的发展成就更趋于缓慢平庸。初盛唐时期,虽有上官仪、初唐四杰、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李白、杜甫等一流诗人参与咏史诗创作,使之音韵流畅、词藻丰瞻,浸染了这一时期诗坛普遍流行的华美之风,但从总体上说囿于情思浅白直露,失落了魏晋以来积淀的深邃厚重的历史精神,故而这一时期的咏史诗也多华而不实之作,失去了魏晋咏史诗那种永恒的内在张力和底蕴。这种情况直到中唐的文化反思时期才有所改观,刘长卿、韦应物、李贺、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一些兼备思想家特质的诗人观今思古、对历史进行严肃深刻的追索和回顾,使中唐咏史诗的思想内涵有了一定拓展,并为晚唐咏史诗的复兴奠定了一定基础。而晚唐虽是多事之秋,国家政局陷于分崩离析之际,但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却在此时进入了“白银时代”:李商隐、杜牧、罗隐这三位天才咏史诗人相继登上诗坛,他们的咏史诗作视野相对狭窄,视角也不无偏激之处,但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个体心灵在宏观历史氛围中的迷惘与脆弱,融深沉阴郁的历史哲学思考于诗歌的固有美感之中,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力量,在中国古代咏史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其它咏史诗人的诗作较为平庸,晚唐咏史诗的创作在总体来说并不能和处于“黄金时代”的魏晋咏史诗相比。
宋代理学盛行,整体文化倾向趋于内敛,文人的躬查自省和逻辑思辩能力空前提高,这种理性化的整体思维模式必然也会在宋代咏史诗的创作活动中有所体现。宋代已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加之理性化思想文化氛围的制约,宋代咏史诗的创作已不复魏晋晚唐时的光彩,进入了咏史诗发展的“青铜时代”:虽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朱熹等宋诗巨擘在咏史诗的创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且在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大大挖掘了咏史诗议史析史的潜质,但是过度强调理性思辩的诗风却使宋代咏史诗弱化了诗歌最基本的想象力和审美空间,令其变得干瘦枯燥,伤害了诗歌最本质的诗性和意境。哲学上的深化和美学上的淡化让宋代咏史诗的发展不再均衡,它慢慢地偏离了纯粹古典诗歌的美学取向而表现出一种异态的审美风格。
元明时期,诗坛没落,山水咏物成为新一代文人诗作的焦点,传统的咏史诗创作衰微不振。到了清代,咏史诗的发展才进入中兴复苏的“英雄时代”:高压的政治环境、严酷的文化专制迫使诗人们把目光从现实社会中收回,投向了深邈的历史。注重实证的朴学的繁荣,也使清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有所更新突破,咏叹历史的重点亦由具体史事、时段迁移到学术化、特定化的史学上,这一时期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袁枚、赵翼等优秀的咏史诗人,其中以赵翼成就为最高。这批咏史诗人往往兼具学者、诗人二重身份于一身,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在创作咏史诗的过程中通常不由自主地展示出学者特有的敏锐学术目光,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在咏史诗的题材和内在洞察力上都比前代有了大幅度扩展。但是,随着学术之风在清代咏史诗创作活动中的逐渐蔓延,咏史诗内蕴的原始诗性更为稀薄了,失去了魏晋晚唐咏史诗的深情与力度,也没有了宋代咏史诗的机辩与妙趣,越来越趋近于格律化的历史学术随笔。清代咏史诗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强烈反差不免为清代咏史诗发展的中兴繁荣局面蒙上一层“畸形”的阴影。
近代是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黑铁时代”:首先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经历的历史问题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朝代都没有出现过的,这就使以往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突然间处于失重失效的状态,诗人们的关注焦点重新转到了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上,无暇再对历史进行充分的潜思和咀嚼。其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整体发展在这一时期陷于僵局,欲革新而不能维持艺术水准,欲持旧而不能有所深化增益,在苦苦挣扎中无可挽回地滑向全面衰落,挟裹在其中的中国古代咏史诗自然也难逃此劫,随之一同落入低谷。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张维屏、龚自珍、朱琦、王闿运、张之洞、樊增祥、蒋智由、谭嗣同、冒广生、王国维、黄侃、柳亚子等人虽也有咏史诗作问世,但多属偶尔草率为之,或拘谨守旧,或轻狂粗率,在总体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和前代咏史诗相提并论。民国以后,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中国古典诗歌在诗坛失去主流地位,以古典诗歌形式咏叹历史的文人传统亦基本宣告结束。
总之,中国古典咏史诗的发展史是和中国古代文人的主观心灵史相互纠葛、密不可分的。它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一方面跟进追踪着历史变化的焦点与热点,另一方面也以史为鉴,折射出千余年来中国古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演进与转折,把历代中国文人面对历史的心灵困惑与解脱或隐或现地展示在诗卷当中,汇成了一部沁透中国古代文人笑与泪、爱与恨的主观心史。
二、咏史诗的基本类型和历史阐释方式
现存的中国古代咏史诗数量惊人,内容形态各异,但大体来说仍然可以归纳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类型。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咏史诗背后所凸现的,是三种各自不同的历史阐释方式,它们彼此相互纠结缠绕,体现并影响了历代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复杂情绪和思考。
1. 感史诗
这类咏史诗更多依赖直观感悟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咏叹历史,侧重对历史的整体渲染和直觉判断,并不过多过深地纠缠于具体微观的历史细节;抒写者也往往借史生情,在诗歌中无所顾忌地表露出自己的历史态度和个人好恶,一任主观情感在诗句中纵横驰骋、恣意宣泄,情绪化的个性完全凌驾于理性化的客观历史规律之上,故不免有粗疏偏颇之讥。但是,“一切历史均为主观史”,从来就没法摆脱人们对于往事的心灵关照。这种意气飞扬、毫无虚伪矫饰之俗的诗化历史,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主观历史都要来得坦率真挚,也更贴近于历史的真谛,如左思的《咏史诗八首》(选一):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⒈
这首诗一开始就沿袭《诗经》手法以比兴开头,用鲜明的景物对比传达出尖锐强烈的视觉反差,并在这种感官刺激的不平衡状态中慢慢地酝酿、积聚着炽热的情感力量,有如地层之下涌动着的滚烫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冲出地壳喷薄而出。接下去便顺理成章地迸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锥心泣血之句,亦是陈述事实,亦是感叹呐喊,用冷峻硬朗如同刀锋一样的语言划开了自己的胸膛,把心灵深处原本最隐蔽的伤痛和无奈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这种悲愤无助的惨痛呼喊不顾一切地抛弃了理智的约束,在情感上近乎绝望疯狂,但却惊心动魄,以最为原始质朴的情感倾诉抓住了读者,引发了他们的心理共鸣。后面的缘由推理“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也来得颇为偏激牵强,更像是一时冲动之下的赌气定性而非心平气和的条理分析,貌似有力,实则偏执强横,插不进他人的半点异见和反驳。透过诗人愤愤不平的主观有色目光,最后的史据“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也变得扭曲起来,离真正的史实相去甚远,还力图对本来复杂难辨的历史表象作一种简单直截的阐述解释。应该说,左思在这首诗中所采用的历史表述手法是相对简单单调的,跳不出率性而为、直抒胸臆的圈子;流露出来的历史观念也是感性单纯的,有时不免有幼稚之感。但是,就是这样一首满含着荒唐言和辛酸泪的短小诗篇,却没有因为强烈的变形夸张而显得滑稽可笑,仍然保持了历史精神的庄严悲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总会侵染上抒写者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这个层面上讲,左思的咏史诗虽然没能鞭辟入里地点评感知汉代历史,但却把晋代寒门士人求功不得、归隐不甘的尴尬心态和盘托出,精彩无比地展示出一代知识分子充满困惑和痛楚的心灵挣扎,也从一个侧面极其真实深邃地折射出那个时代压抑与自由同在、才气与荒谬并存的精神之光。
2. 述史诗
这类咏史诗主要用以一种克制隐忍的目光来捕捉历史、剪辑历史,并不把自己的主观历史态度明显地表露在诗句当中,而是有选择地把一个个剪影似的静止历史画面拼合在一起,透过这种屏风式的固定视角画面组合来委婉地传达诗人的某种微妙难言的复杂历史情绪。这种言不欲尽的做法看似隐晦,实则深彻,相当深沉地揭示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定性和不可知性,把主观原始历史的那种自带的朦胧和神秘悉数保留下来,建构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美学风格,如李商隐的《吴宫》:
“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⒉
这首诗通篇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个体历史人物特写,只是选取了四处具有特定代表意义的吴宫旧时场景加以排列组合,诗人本人则缄默不语、不予评说,只是把视角一步步地按自己的意愿推近拉远,把自己的所见之物不紧不慢地复述给读者,由读者自己去感悟判断。诗人首先在想象中远眺到了吴宫“龙槛沉沉水殿清”的沉寂远景,在一种宏大庄重的氛围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繁华背后可能潜在的寂落和孤独,接着又把镜头拉近到全景“禁门深掩断人声”,进一步渲染了吴宫的庄严肃穆和冷清寂静,以致于人的个体性活动完全被巨大的建筑物“吴宫”所吞没掩盖,变得了无痕迹、无声无息。此时的“吴宫”已不再单纯地作为某个庞大的古代宫殿而存在,而是变成了一种整体宏观历史的象征,映照出个体人类活动的渺小和无力。后面又把镜头拉近到深宫内部的近景“吴王宴罢满宫醉”,多少添加了几份欢愉,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宴罢之时虽然众人皆欢,气氛达到高潮,但同时也是由盛而衰、由喜转悲的开始,暗示着大规模的败亡还埋伏在后面。最后一笔“日暮水漂花出城”则突然把镜头由近拉远,视点随着飘落在护城河水中的宫花重新由宫内流淌回了宫外,“一切都会过去”,不管是曾经辉煌的落日、几时盛开的鲜花还是现在还巍峨耸立着的宫殿,最终都会归于凄凉冷清的宁静,在浩渺无边的历史面前,一切的繁华和美丽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来自个人的感叹和评论也变得那么短浅可笑,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到历史深厚雄浑的神秘内核,与其就事论事地在历史面前坐而论道,还不如彻底沉默,把自己眼中所见、心中所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复原出来,留待后人自己去体味言说。这种做法看似苍白平淡、冷漠无味,实则蕴含了极深的历史智慧:历史,本来就是主观多变的,每个人心中的历史都各自不同,谁也没有能力洞悉整个历史的全部真谛,至多只能对其中某一部分历史真相有所体察感悟。既然孤立的个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穷尽历史,那反而不如在历史面前全身而退,把诉说想象的空间留给其他个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填补。每个人在看待历史的时候都有着浅薄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着深刻的一面,各人的深刻各有不同,并无太过明显的高下之分。也许只有把无数个体的历史观念汇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勾勒出历史真相的大致轮廓。因此,李商隐这首《吴宫》虽然没能明确地表示出自己的历史态度,但却把历史思考和评价的空间留给了后来的无数读者,解放了读者的历史话语权力,从而构筑了一种开放流动的主观历史模式,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唐文人逸出群体束缚且日益强大起来的主观个体意识。
3. 议史诗
这类咏史诗自宋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主要强调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剖析历史、解读历史,惯于对具体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并把这一整套思辨过程完整地铺展在诗句当中,理性因素和逻辑思维的加强使诗人们的历史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通常别出新见、自成其理,但却相应地弱化了诗歌中最为本质的情感因素,也使咏史诗的内在指向变得单一狭隘起来,往往流于浅白尖刻,失去了前代咏史诗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天悯人和浑厚深沉,如赵翼的《修史漫兴》:
“史局虚惭费月餐,古今历历作闲观。千秋于我宜何置,寸管论人固不难。高焰辉檗红烛炬,古香浮砚翠螺丸。只输小宋风流处,少个浓妆伴夜阑。”⒊
这首诗的咏史重点已经由具象的个别史事转移到了抽象的普遍史学之上,对历史的理解观察较前代有了一些新颖深刻之处,视角也更为广阔宽泛。但却在历史观念上对前代大加颠覆,在嬉笑揶揄之中解构了庄严肃穆的传统历史精神,在历史情感上近乎于稀薄冷淡,更多依赖精警的历史观点来说服读者,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依靠深厚真挚的情感来感染读者,打动读者。最开头便以“史局虚惭费月餐”的玩世态度开场,把观念化的史学和物质化的衣食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在怪诞化的比较中揭示了主观历史的某种虚无荒诞性,次句“古今历历作闲观”则把诗人自己和主观历史完全割裂开来,完全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来把玩历史、赏鉴历史,这种做法看似潇洒冷静,实则狭隘片面:历史,本身就是连续不断的,它不仅覆盖了过去,贯穿了现在,还会延续到将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逃出历史的笼罩置身事外,而只能随着历史大环境的变化在漩涡中起起伏伏,昨天在他人身上发生过的,今天就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再次发生,谁都没有权力在历史面前故作轻松地充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看客,那样不过是公开了自己的肤浅和麻木。而后的颔联“千秋于我宜何置,寸管论人固不难”则充分认识到了主观历史的人为性和随意性,肯定了历史抒写者对主观历史的绝对支配权力,把历史抒写者的主体地位完全凌驾于主观历史之上,显示了一定的历史洞察力和独到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是,刻意撇清自己、保持理性的赵翼恰恰忽略了:主观历史与历史抒写者是相互造就、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历史抒写者编写创造着历史,在主观历史上打上自己的深深烙印,另一方面主观历史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改造着历史抒写者,无形地把他们融化吸收在内。一个不能投入自我、融入自我的历史抒写者必定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历史抒写者,也很难创作出一部成功的主观历史,这对于抒情至上的咏史诗歌来说则更是如此。所以,过度强调历史抒写者地位的行为虽有一定道理,但总体来说仍然失之偏颇。最后的四句“高焰辉檗红烛炬,古香浮砚翠螺丸。只输小宋风流处,少个浓妆伴夜阑。”则颇有冷嘲反讽的味道,把抒写历史的活动和自己本能的情欲性欲联想起来,从而彻底消解了传统历史抒写活动的严肃意义,将主观历史的荒诞特质推向顶峰,在历史抒写过程中注入了某些喜剧性甚至是闹剧性因素,传统咏史诗原有的悲情特质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应该说,赵翼在这首《修史漫兴》中反复探讨主观历史之荒诞性和随意性的做法把对历史的认识从反思层面提升到了哲学层面,眼光新颖独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补充了传统的“人史关系”,就某些方面来说确有深刻之处。但是,这种对历史哲学的过度迷恋却最终把情感因素排斥在历史认识的范畴之外,将原本丰腴醇美的咏史诗歌强行抽剥成了一组不无偏执的历史概念组合,使其失去了诗歌最基本的意境和韵味,轻佻有余,回味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清中期文人已经趋于僵化干涩的“学术化”思想倾向与诗坛风气。
通过以上的归纳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咏史诗总结划分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咏史诗歌由远及近,依次繁荣兴盛起来,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不断演进变化、逐渐由感性向理性过渡的历史认知模式。在咏史诗歌的流动变化中,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的“历史”概念也慢慢从繁复庞杂的主观思想中单独分离出来,一步步走向清晰稳定。然而原始历史中原本蕴含的浓郁诗意却在历史理性的不断压迫下日益沉沦萎顿,最终消弭殆尽。
三、咏史诗的历史观念与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咏史诗是在一代代杰出诗人延续不断的感悟吟咏下逐渐成熟兴盛的,汇集了无数诗人对于历史的个体心灵回应。这些长年积累在一起的主观个体历史精彩纷呈、个性毕现,往往站在不同的角度并用各自不同的口吻来观察历史、解释历史,闪烁于其中的历史观念也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很难从中寻觅到较为突出的共性思想特质,反倒暗示出中国历代咏史诗人种种无法解脱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
首先在历史认知观上,中国古代咏史诗作历来存在“历史可知观”和“历史不可知观”的矛盾。持“历史可知观”的咏史诗人大都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力求把握宏观历史的整体规律走向,往往一针见血地点出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着力推翻并纠正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主观历史成见,思辨精辟清晰,态度冷峻沉稳,把主观情感高度克制到近于客观的程度,还有意识地放大了历史的必然性因素,如罗隐的《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⒋ 而持“历史不可知观”的咏史诗人则一般从个人情感的微观视角出发,力图揭示个体心灵在历史大环境压迫下的徘徊反复,也通常非常真挚地表现出个人在与历史对抗过程中的孤独和无奈,更重于直接倾诉瞬间的自我感悟和思索,情感深沉婉转,态度犹豫矛盾,将自己复杂厚重的主观情感不加掩饰地释放出来,把目光集中在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上,如李商隐的《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⒌ 应该说,历史的可知论与历史的不可知论都各有其狭隘之处,同时又各有其深刻之处,因为历史原本就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既是可知的,也是不可知的。但对于在历史漩涡中苦苦挣扎的个人来说,历史不可知的一面要大过可知的一面,总是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料、突如其来的因素。在这些变数面前,来自个人的回避和抵抗是那么微弱无力,只能无可奈何地全盘接受,并在被迫接受的过程中疑惧反思。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的不可知性”可能并不比“历史的可知性”来得更加睿智深刻,但却更为切近自然,相当真实地展现了具体个人在宏观历史之下的渺小与无助,因而也在擅于呈现主观个性的古典咏史诗歌中抒发得更为充分。
其次在历史范畴观上,中国古代咏史诗作也长期存在“历史有限观”和“历史无穷观”的争议。流露出“历史有限观”的诗作一般认定历史的容纳总量有所限度,并执着于追寻历史惊人的一致性因素,将其构合成一种稳定的循环模式,主要把经由岁月冲刷而得以保存的重大历史事件排列在模式之内,不令其有所游离散逸,洞察深刻且举重若轻,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的某种动因和源头,如白居易的《咏史》:“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⒍ 而表现出“历史无穷观”的诗作则认为历史即等同于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不仅容纳总量无穷,而且也和日常生活一样零碎庞杂、变化多端,可能抓住的只有浮光掠影的表面,实际的来由根源则很难让人真正摸清,因此更陶醉于抓拍历史的某个片断并随心所欲地谈论点评,丝毫不考虑评论是否妥帖得当,但往往慧眼独具、别有新意,如李商隐的《南朝》:“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⒎ 实事求是地讲,历史有限观的确要比历史无穷观来得更为精准。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主观映射,免不了要有意识地选择和遗忘,这就决定了历史永远不可能和无边无际的日常生活相重合,而只能是对它的提纯和过滤。但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⒏ 。史学意义上的“精确历史”和诗学意义上的“模糊历史”所采用的价值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诗人眼中的“模糊历史”可能并不可靠,然而却不能不令读者心醉神迷:它用“以有限观无穷”的方式充分揭示出人类主观感知的缥缈和短暂,把混沌朦胧状态下的自足之美悉数保留下来,以浑厚神秘的多重内涵来吸引读者、感染读者,而这与中国古典咏史诗的蕴藉特质正相吻合。
再次在历史本质观上,中国古代的咏史诗作还一直有着“史理本质观”和“史情本质观”的分歧。在同时认可历史主观性的前提下,渗透“史理本质观”的诗作认为历史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只有在经历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严密加工之后才真正得以形成。它残酷而稳定,只是按照自己特有的一套独立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进行到底,根本不以人的意志需要为转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压迫、毁灭个体,如崔颢的《霍将军》:“长安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日晚朝回拥宾从,路傍揖拜何纷纷。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一朝天子赐颜色,世上悠悠应自知。”⒐ 而浸染“史情本质观”的诗作则论定历史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充盈和再现,倘若心中存情便可下笔成史,根本无须考虑理性的束缚和干扰,更不可能机械地依赖理性因素去解释历史中所发生过的一切。主观历史也往往随着个人的情绪变化而不断飘忽转移,亦正亦邪,亦美亦丑。真正的历史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而只能分散地存在于各人心中,各人心中的历史亦各自不同,没有个人的喜怒哀乐,便没有历史的兴亡盛衰。能够生生不息的,只有和独立个体精神缠绵在一起的主观历史,如李绅的《长门怨》:“宫殿沈沈晓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⒑ 事实上,理性的历史和感性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它们统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成完整的历史。但是,“完整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可以无限企及却始终难以达到的理想存在,任何人类所创造运用的历史作品和历史理念都难免片面之嫌。在这个意义上,以情为本的主观历史虽然有模棱两可、短暂不定的片面性,但却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揭示了个性化的阐释接受在历史生成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因而更容易与张扬个性的中国古典诗性精神相契合。
所以,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观念和思想内涵是极其驳杂丰富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有很强的“不可言说性”:它既自相排斥,又互相依存;既直爽干脆,亦犹豫彷徨;既清醒无比,也荒谬绝伦,将中国古代文人数千年来饱含血泪的心灵印迹完全铺展开来,绘成了中国古代主观情感历史的壮丽画卷。在这波澜壮阔的画卷之中,客观历史和主观心灵中的种种光明与阴暗、美丽与丑陋难舍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只能留待后人自己去品味评说。
作者结语: 《写在精神泯灭的时代》
当现实不复辉煌的时候,
我们还拥有历史;
当历史黯然失色的时候,
我们还拥有激情;
当激情燃烧殆尽的时候,
我们还拥有信念;
当信念颓然倒地的时候,
我们还拥有什么?
(原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09年第15期作论点摘编)
⒈左思《咏史》: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晋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P733
⒉李商隐《吴宫》: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四十,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97
⒊赵翼《修史漫兴》:载《瓯北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P164-165
⒋罗隐《西施》:载《全唐诗》第十九册卷六百五十六,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7545
⒌李商隐《马嵬》: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77
⒍白居易《咏史》:载《全唐诗》第十四册卷四百五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5129
⒎李商隐《南朝》:载《全唐诗》第十六册卷五百四十,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6183
⒏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二》: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⒐崔颢《霍将军》:载《全唐诗》第四册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1323
⒑李绅《长门怨》:载《全唐诗》第十五册卷四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P5496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