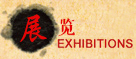新德里“鲁迅文化周”散记 黄乔生
发布日期:2013-11-11 浏览数:
哦,去印度了。取了什么经回来?
这是我从印度回来后,与朋友们谈起,他们往往要打趣的话。是啊,虽然是第一次去印度,但口气中却显得对印度很熟悉似的,这恐怕是受了《西游记》和玄奘故事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印度的情况很陌生。一周多的时间,而且只在新德里一个城市,参观了古迹和博物馆,逛了几家商店和市场,坐着被称为“陆上飞机”的小三轮,在车流中攒行,真所谓走马观花了。脑子里所能搜出的,只有一些散漫的片段,无论如何与“经”不沾边。
这次,我率鲁迅博物馆代表团到印度参加“鲁迅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动包括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印度尼赫鲁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鲁迅博物馆送去的《鲁迅生平展》,是鲁迅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11月15日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隆重开幕。此外还有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电影赏析、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学生自编自演与鲁迅及其著作相关的舞台剧、公开讲座等活动。
我们大学校园里漫步,一个很大的绿油油的校园,有些地方还有野趣,松鼠到处穿行,自不待言。各种花草,我们多数叫不上名字,古树盈抱,触目皆是。遇到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亚系的教授,带我们参观教学楼,并且到他的办公室座谈片刻。
我们还参观了图书馆中文书部分。中文书太少,我们当即决定把携带的图书捐给了图书馆。把携带的一套鲁迅著作初版本精选丛书赠送给印度中国研究中心。但事后想,这也存在问题。他们是英语国家,应该有英语书,才更适合他们。在随后举办的学术会上,我也向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资料问题。因为印度是英语国家,主要是英文资料,中文资料缺少。他们从哪里获得参考资料的呢?老教授这一代人,中文可能不好,又不大熟悉网络,所以资料的获得很成问题。这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当年鲁迅对泰戈尔产生一些误解,就因为没有看到作品的翻译。
大家对教授讲的亚洲共同体,规模仅次于世界银行的亚洲银行,与欧元相当的亚元等等的兴趣,不如对校园里的各种招贴的兴趣大。大多是左派标语和革命者如切格瓦拉的画像。有些是讽刺和抨击大财团,有的指斥政府,其中地产商开发项目成为攻击的一个重点对象。据引领我们参观的印度朋友介绍,这些年印度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建设项目不断上马,用地量大增,势必要拆迁征用土地,引发开发商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争端。印度本来左翼思想较盛,印度共产党虽然没有取得全国执政权,但在有些重要城、邦有相当大的优势。例如在加尔各答执政长达三十多年。然而,去年印共在这里失去了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开发征地造成冲突,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在选举中失利。
邀请我们来印度的尼赫鲁大学汉语系的海孟德老师做了周到的安排。他的学生们跑前跑后,安排我们的食宿,引领我们参观,对中国充满了好奇,纷纷表达想到中国学习的愿望。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印的文化交流并不十分热烈,这当然是与我们的东邻日本、韩国相比较而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一位日本九州大学的老师跟我谈起来,说他也是第一次到印度,感到印度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了解很少。这也印证了我的观感。因此,我在鲁迅生平展开幕式上致辞中先说了一番套话: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既古老又充满新生的活力,都具有博大、深沉的品质。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公元六世纪,印度的达摩禅师到中国,建立了禅宗教派,影响深远。中国唐代的玄奘,‘西天取经’,远赴印度,取回经书,悉心翻译,为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很多仁人志士,向各国取法,鲁迅就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翻译了大量外国著作,被誉为‘现代玄奘’。但是,在近现代,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成果却不多,因而产生一些误解。鲁迅对泰戈尔的一些误解,就是因为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翻译,没有交流。我提出,当今中印文化界人士,要学习达摩、玄奘、鲁迅等前辈,以旺盛的求知欲、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从事于文化交流,研究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探讨深化交流的途径,使两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更有建设性。随后表达了认真学习印度文化、了解印度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鲁迅研究的状况和成果的意愿。我说,唐朝的高僧本来是想到西方取经的(A pilgrimage to west),却到了南方邻国印度;清朝的鲁迅本来想学习西方文化的,却到了东邻日本。这两个“设远求近”的例证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东西,无论远近,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印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对鲁迅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现状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研讨会分为几个部分。总体上说,现在的鲁迅研究,对象不是鲁迅,而是研究鲁迅,也就是鲁迅研究的研究。这从很多题目中看得出来,例如研究鲁迅著作改编的,研究后人的鲁迅的评价即所谓“鲁迅崇拜”或曰“鲁迅神话”的。探讨鲁迅与孔夫子的单元“鲁迅、孔夫子和新社会主义文化”,着重在当前孔子热与鲁迅的比较,指出了一种将鲁迅和孔子弥合起来的倾向。我两年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批林批孔时期对鲁迅著作的利用的文章,恐怕也是有这样的倾向的。可惜几位印度学者可能不懂得中文,故几乎很少引用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几部(篇)有关论著。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文豪鲁迅的圣化和崇拜,并没有一味从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从文学的神圣性角度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这是很难得的.
还有不少印度学者,比较鲁迅与印度作家的成就,如普赖姆昌德、普都麦皮坦、姆克提波德的作品,特别注意与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刻画。
有的论文颇有新意,如日本学者从鲁迅协写作野草时期报刊上的发表的文章入手,对野草接受影响的研究,中国革命的死后生命存在形式,探讨了五四时期仪式和政治的对话机制。探讨了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一个是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政治话语,一个是传统的民间信仰的话语,认为他们表面上呈现巨大差异,实际上却都纠缠于一个共同的主题“永恒”。这可以揭示一种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尽管可能是以一种不直接相关的方式。
在印度召开一个关于文学家的研讨会,不能不谈到泰戈尔,印度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而且曾来过中国,引起轰动,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作家。据中国研究所的同仁说,2013年泰戈尔获诺奖100周年的时候,要举行更多的活动。中国的出版机构要出版《泰戈尔全集》,那时,更会有一番热闹的景象吧。泰戈尔比鲁迅大二十岁,算是前辈了。泰戈尔或诺奖,鲁迅则说自己不配,拒绝提名。应该很景仰泰戈尔才对,但给人的印象是,鲁迅对他没有好声气,讽刺挖苦,什么“竺震旦”啦,远没有后来接待萧伯纳时的热情。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狄伯杰教授在《鲁迅对泰戈尔的批评:理解与误解》中,全面梳理了这个问题提出两人的背景不同,环境不同,一个是要想西方学习,一个则是要保护固有文化,一个对孔子致敬,一个在打孔家店,一个是反暴力,一个是赞赏苏联,提倡暴力。所以鲁迅对泰戈尔表现了反感,冷淡和嘲讽。我提交的论文与狄伯杰教授的内容有关,在会上也做了一些讨论。还有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也提交了韩国对泰戈尔和鲁迅的接受比较的论文。提供了泰戈尔与韩国文士交往的事实。我的论文题目是《“但除了印度”:鲁迅对印度的想象》也与泰戈尔有关。我从1925年《京报副刊》向文化教育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目事件说起。鲁迅当时的回答很奇特,“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随后加的一段注解中提到印度:“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在众多“外国”中,印度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者之一,为什么鲁迅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么,印度的书是否也像中国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劝人出世,而使读者与“实人生离开”呢?或者,印度的书还有别的问题?鲁迅没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确说出来。
问题是:鲁迅在写这段话之前,究竟看过多少有关印度的书?他对印度文化的印象来自何处?在写下这五个字的时候,鲁迅的脑海中是有泰戈尔的影子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泰戈尔来华发表的言论,特别是中国一些文人对泰戈尔的吹捧很反感,发表了多个议论。还有他对印度的现实也有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述,如“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
我的论文追溯了鲁迅对印度文化的评价。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关注印度,对印度古代文学十分推崇,在自己的佛学、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不断致以赞美。然而他对近代印度是悲观的,认为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彻底衰败,成为“影国”。他极想了解印度,但限于条件,对在印度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了解太少,只是到了晚年,才从媒体上看到甘地的事迹,给予赞美。
至于他对泰戈尔的误解。我认为,鲁迅在讽刺嘲弄围绕在泰戈尔身边的文人学者的同时:“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其实,仍然保有理性的看法,从来没有在这幅漫画中的泰戈尔身上涂抹污水。他只有一个地方误解了泰戈尔,那就是他听信了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传述。“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虽然只有这一处误解,但却是很重大的,因为涉及人道的根本问题。其原因,除了爱罗先珂,也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不了解有关。例如如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发表的《人的文学》中,在反对中国乃至东方束缚人性的“非人”的文学时,就批评道:“印度诗人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她的‘心的撒提’(Sutteo,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孀与她丈夫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因为这样的印象,鲁迅对印度现代社会的印象,不但是神秘,而且还有其他一些负面的因素,导致他特别写下那五个字,把印度排除在文明国家之外。
一方面因为没有实际的接触,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做参考,导致他在评论印度时只能凭想象和他人的不完整甚至不正确的材料。当时,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
鲁迅总有一种预感,印度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她的文明是伟大的。鲁迅青年时代,一些中国人看不起印度,以为它不如中国。鲁迅更多自省意识,告诫中国人不要盲目乐观。因此,他对印度还保留着敬畏,对甘地等杰出人物是赞赏的。甚至对泰戈尔,鲁迅也注意到他本人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我是鲁迅离开北京,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肯定他代表印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鲁迅晚年也还在留心搜集有关印度的书籍。我们这次之作展览,就把鲁迅收藏的有关印度的书籍及印度翻译的鲁迅著作。文明古国,现代沦为“影国”——中国也有一半在阴影中——是极惨痛的事实,他一生奋斗,谋求摆脱阴影,寻求光明,正同印度的贤哲相通。
最后说印度之行引发了很多思考,感到他们的质朴热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真纯和求知欲望。尼赫鲁大学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除了语言类科系招收本科生外,其他都是硕士博士。他们的演出鲁迅生平和著作改编的短剧,我们看了《药》和《阿Q正传》,把握得比较到位,说的汉语也堪称字正腔圆。他们颇为聪明。那天我们参观东亚系时,特意到中文系,与学生们交流,我问他们有没有中国老师,他们说以前曾有过,但现在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很多印度同学还没有中文名字,于是就嚷着请在场的几位中国学者为他们起名,结果一发不可收,不断有学生来求名问字。单是我,就命名了四五位,几乎把学问用尽——回想起来,这是印度之行的一个颇有意味的插曲。
这是我从印度回来后,与朋友们谈起,他们往往要打趣的话。是啊,虽然是第一次去印度,但口气中却显得对印度很熟悉似的,这恐怕是受了《西游记》和玄奘故事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印度的情况很陌生。一周多的时间,而且只在新德里一个城市,参观了古迹和博物馆,逛了几家商店和市场,坐着被称为“陆上飞机”的小三轮,在车流中攒行,真所谓走马观花了。脑子里所能搜出的,只有一些散漫的片段,无论如何与“经”不沾边。
这次,我率鲁迅博物馆代表团到印度参加“鲁迅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动包括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印度尼赫鲁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鲁迅博物馆送去的《鲁迅生平展》,是鲁迅文化周的重要活动之一,11月15日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隆重开幕。此外还有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电影赏析、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学生自编自演与鲁迅及其著作相关的舞台剧、公开讲座等活动。
我们大学校园里漫步,一个很大的绿油油的校园,有些地方还有野趣,松鼠到处穿行,自不待言。各种花草,我们多数叫不上名字,古树盈抱,触目皆是。遇到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亚系的教授,带我们参观教学楼,并且到他的办公室座谈片刻。
我们还参观了图书馆中文书部分。中文书太少,我们当即决定把携带的图书捐给了图书馆。把携带的一套鲁迅著作初版本精选丛书赠送给印度中国研究中心。但事后想,这也存在问题。他们是英语国家,应该有英语书,才更适合他们。在随后举办的学术会上,我也向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资料问题。因为印度是英语国家,主要是英文资料,中文资料缺少。他们从哪里获得参考资料的呢?老教授这一代人,中文可能不好,又不大熟悉网络,所以资料的获得很成问题。这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当年鲁迅对泰戈尔产生一些误解,就因为没有看到作品的翻译。
大家对教授讲的亚洲共同体,规模仅次于世界银行的亚洲银行,与欧元相当的亚元等等的兴趣,不如对校园里的各种招贴的兴趣大。大多是左派标语和革命者如切格瓦拉的画像。有些是讽刺和抨击大财团,有的指斥政府,其中地产商开发项目成为攻击的一个重点对象。据引领我们参观的印度朋友介绍,这些年印度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建设项目不断上马,用地量大增,势必要拆迁征用土地,引发开发商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争端。印度本来左翼思想较盛,印度共产党虽然没有取得全国执政权,但在有些重要城、邦有相当大的优势。例如在加尔各答执政长达三十多年。然而,去年印共在这里失去了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开发征地造成冲突,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在选举中失利。
邀请我们来印度的尼赫鲁大学汉语系的海孟德老师做了周到的安排。他的学生们跑前跑后,安排我们的食宿,引领我们参观,对中国充满了好奇,纷纷表达想到中国学习的愿望。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印的文化交流并不十分热烈,这当然是与我们的东邻日本、韩国相比较而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一位日本九州大学的老师跟我谈起来,说他也是第一次到印度,感到印度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了解很少。这也印证了我的观感。因此,我在鲁迅生平展开幕式上致辞中先说了一番套话: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既古老又充满新生的活力,都具有博大、深沉的品质。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公元六世纪,印度的达摩禅师到中国,建立了禅宗教派,影响深远。中国唐代的玄奘,‘西天取经’,远赴印度,取回经书,悉心翻译,为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很多仁人志士,向各国取法,鲁迅就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翻译了大量外国著作,被誉为‘现代玄奘’。但是,在近现代,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成果却不多,因而产生一些误解。鲁迅对泰戈尔的一些误解,就是因为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没有翻译,没有交流。我提出,当今中印文化界人士,要学习达摩、玄奘、鲁迅等前辈,以旺盛的求知欲、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从事于文化交流,研究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探讨深化交流的途径,使两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更有建设性。随后表达了认真学习印度文化、了解印度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鲁迅研究的状况和成果的意愿。我说,唐朝的高僧本来是想到西方取经的(A pilgrimage to west),却到了南方邻国印度;清朝的鲁迅本来想学习西方文化的,却到了东邻日本。这两个“设远求近”的例证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东西,无论远近,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印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对鲁迅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现状的认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研讨会分为几个部分。总体上说,现在的鲁迅研究,对象不是鲁迅,而是研究鲁迅,也就是鲁迅研究的研究。这从很多题目中看得出来,例如研究鲁迅著作改编的,研究后人的鲁迅的评价即所谓“鲁迅崇拜”或曰“鲁迅神话”的。探讨鲁迅与孔夫子的单元“鲁迅、孔夫子和新社会主义文化”,着重在当前孔子热与鲁迅的比较,指出了一种将鲁迅和孔子弥合起来的倾向。我两年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批林批孔时期对鲁迅著作的利用的文章,恐怕也是有这样的倾向的。可惜几位印度学者可能不懂得中文,故几乎很少引用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几部(篇)有关论著。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文豪鲁迅的圣化和崇拜,并没有一味从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从文学的神圣性角度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这是很难得的.
还有不少印度学者,比较鲁迅与印度作家的成就,如普赖姆昌德、普都麦皮坦、姆克提波德的作品,特别注意与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刻画。
有的论文颇有新意,如日本学者从鲁迅协写作野草时期报刊上的发表的文章入手,对野草接受影响的研究,中国革命的死后生命存在形式,探讨了五四时期仪式和政治的对话机制。探讨了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一个是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政治话语,一个是传统的民间信仰的话语,认为他们表面上呈现巨大差异,实际上却都纠缠于一个共同的主题“永恒”。这可以揭示一种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尽管可能是以一种不直接相关的方式。
在印度召开一个关于文学家的研讨会,不能不谈到泰戈尔,印度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而且曾来过中国,引起轰动,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作家。据中国研究所的同仁说,2013年泰戈尔获诺奖100周年的时候,要举行更多的活动。中国的出版机构要出版《泰戈尔全集》,那时,更会有一番热闹的景象吧。泰戈尔比鲁迅大二十岁,算是前辈了。泰戈尔或诺奖,鲁迅则说自己不配,拒绝提名。应该很景仰泰戈尔才对,但给人的印象是,鲁迅对他没有好声气,讽刺挖苦,什么“竺震旦”啦,远没有后来接待萧伯纳时的热情。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狄伯杰教授在《鲁迅对泰戈尔的批评:理解与误解》中,全面梳理了这个问题提出两人的背景不同,环境不同,一个是要想西方学习,一个则是要保护固有文化,一个对孔子致敬,一个在打孔家店,一个是反暴力,一个是赞赏苏联,提倡暴力。所以鲁迅对泰戈尔表现了反感,冷淡和嘲讽。我提交的论文与狄伯杰教授的内容有关,在会上也做了一些讨论。还有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宰雨也提交了韩国对泰戈尔和鲁迅的接受比较的论文。提供了泰戈尔与韩国文士交往的事实。我的论文题目是《“但除了印度”:鲁迅对印度的想象》也与泰戈尔有关。我从1925年《京报副刊》向文化教育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目事件说起。鲁迅当时的回答很奇特,“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随后加的一段注解中提到印度:“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在众多“外国”中,印度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者之一,为什么鲁迅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么,印度的书是否也像中国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劝人出世,而使读者与“实人生离开”呢?或者,印度的书还有别的问题?鲁迅没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确说出来。
问题是:鲁迅在写这段话之前,究竟看过多少有关印度的书?他对印度文化的印象来自何处?在写下这五个字的时候,鲁迅的脑海中是有泰戈尔的影子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泰戈尔来华发表的言论,特别是中国一些文人对泰戈尔的吹捧很反感,发表了多个议论。还有他对印度的现实也有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述,如“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
我的论文追溯了鲁迅对印度文化的评价。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关注印度,对印度古代文学十分推崇,在自己的佛学、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不断致以赞美。然而他对近代印度是悲观的,认为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已彻底衰败,成为“影国”。他极想了解印度,但限于条件,对在印度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了解太少,只是到了晚年,才从媒体上看到甘地的事迹,给予赞美。
至于他对泰戈尔的误解。我认为,鲁迅在讽刺嘲弄围绕在泰戈尔身边的文人学者的同时:“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其实,仍然保有理性的看法,从来没有在这幅漫画中的泰戈尔身上涂抹污水。他只有一个地方误解了泰戈尔,那就是他听信了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传述。“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虽然只有这一处误解,但却是很重大的,因为涉及人道的根本问题。其原因,除了爱罗先珂,也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不了解有关。例如如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发表的《人的文学》中,在反对中国乃至东方束缚人性的“非人”的文学时,就批评道:“印度诗人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她的‘心的撒提’(Sutteo,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孀与她丈夫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因为这样的印象,鲁迅对印度现代社会的印象,不但是神秘,而且还有其他一些负面的因素,导致他特别写下那五个字,把印度排除在文明国家之外。
一方面因为没有实际的接触,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做参考,导致他在评论印度时只能凭想象和他人的不完整甚至不正确的材料。当时,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
鲁迅总有一种预感,印度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她的文明是伟大的。鲁迅青年时代,一些中国人看不起印度,以为它不如中国。鲁迅更多自省意识,告诫中国人不要盲目乐观。因此,他对印度还保留着敬畏,对甘地等杰出人物是赞赏的。甚至对泰戈尔,鲁迅也注意到他本人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我是鲁迅离开北京,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肯定他代表印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鲁迅晚年也还在留心搜集有关印度的书籍。我们这次之作展览,就把鲁迅收藏的有关印度的书籍及印度翻译的鲁迅著作。文明古国,现代沦为“影国”——中国也有一半在阴影中——是极惨痛的事实,他一生奋斗,谋求摆脱阴影,寻求光明,正同印度的贤哲相通。
最后说印度之行引发了很多思考,感到他们的质朴热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真纯和求知欲望。尼赫鲁大学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除了语言类科系招收本科生外,其他都是硕士博士。他们的演出鲁迅生平和著作改编的短剧,我们看了《药》和《阿Q正传》,把握得比较到位,说的汉语也堪称字正腔圆。他们颇为聪明。那天我们参观东亚系时,特意到中文系,与学生们交流,我问他们有没有中国老师,他们说以前曾有过,但现在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很多印度同学还没有中文名字,于是就嚷着请在场的几位中国学者为他们起名,结果一发不可收,不断有学生来求名问字。单是我,就命名了四五位,几乎把学问用尽——回想起来,这是印度之行的一个颇有意味的插曲。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