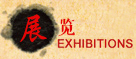现存鲁迅藏书共4000余种、14000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946种7579册,中文平装书866种1112册,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页),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95种1889册。中文藏书中,线装书籍占的比例最大。其中颇有几种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知不足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等等。鲁迅藏书虽算不上宏富,但其价值不容忽视,从中或可略窥一代文豪学术文章的特点。《四部丛刊》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在鲁迅学术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值得注意。
一
清代的乾隆皇帝将历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定名为“二十四史”,全书3249卷,约四千万字。这些史书由官方修撰,以大致统一的纪传体编写,历朝视之为正统史书,故又称“正史”。《二十四史》记录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550年),下迄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长达四千多年间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篇幅宏伟,史料丰富,堪称中华文化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文献。
“二十四史”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清乾隆皇帝的所谓钦定版《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简称“殿本”),流布最广。其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遵从皇帝意见,坚持政治正确,因而有意无意的错讹很多,甚至有段落颠倒、整段脱落等现象。李岳瑞在《悔逸斋笔乘》中说:“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为了取悦皇帝,故意留下些明显的错误,呈给喜欢校书的乾隆,期待皇帝看出错误,降旨申斥馆臣的“不学”,并怡然自觉学问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但不幸的是,“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清朝末年由金陵、浙江、江苏、湖北、淮南五个地方官书局联合刻印的“局本”在质量上胜过殿本,然终难与钦定御制角力。
降至民国,中华书局排印的“聚珍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各领风骚。
中华书局的“聚珍本”《二十四史》以“殿本”为校印底本,铅字排印出版。1920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备辑印《四部备要》,全书11305卷,分订为2500册。中华书局选择了丁辅之的“聚珍仿宋体”排版。《四部备要》出版后,很受欢迎。1930年11月,中华书局发布《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样本》,决定单独发行二十四史。其“校印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缘起”声明该书“字体大”、“印刷精”、“版式雅”、“售价廉”。为了方便普通读者阅读和研究,“聚珍版”在注释较多的“前四史”中,采用二号方体字印制正文,三号长体字印制注释,醒目悦目。其余各史,由于注释极少,以四号方体字印制。五开大本,天宽地阔,便于批注。
因为只是将已经出版的《四部备要》“史部”中的《二十四史》抽出,加大开本印制即可,因此,中华版的二十四史制作迅捷,发售顺畅。
“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张元济(1867—1959)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斥巨资广搜博采各史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始告竣工。“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珍罕版本因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编校者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如僧人之“百衲衣”,故而得名。
1930年3月,商务印书馆正式发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其中的“影印缘起”,记述了这部经典版本的诞生经过。1920年,商务印书馆开始辑印“四部丛刊”,进行途中,编辑者即注意到《二十四史》存在版本问题。但因一时找不到更好版本,不得已用“殿本”为底本影印。后经张元济多方搜求,逐渐汇集到一部分宋元古本。1926年“四部丛刊”重印时,商务印书馆发布预告称,除《明史》仍用殿本之外,其它各史都将以珍罕的宋元古本为底本影印。1930年,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以宋版古本影印的同时,商务印书馆正式宣布“百衲本”《二十四史》公开发售。
按预售计划,“百衲本”《二十四史》应当在1933年全部出齐。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导致已经印制好的大量图书、印版焚毁,甚至连馆藏的宋元古本也未能全部抢救运出。到1934年间,除了“一二八”事变之前已经印制完毕并按预约售出的前两批六种史书,以及刚印制完成的第三批四种共计十种史书之外,其余“十四史”均需重新制版,有的还需重新搜求古本。商务印书馆同仁全力以赴、共克时艰,学术、藏书等各界人士鼎力襄助,使这项伟大的工程没有中辍。张元济于1934年3月发布了“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预约样本。全书至1936年出齐。
中华书局排印“聚珍本”《二十四史》针对普通读者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针对专业读者的需求。一个有美观雅致的字体版式,一个有精益求精的描润校印,各具特色。论享受阅读,要看“聚珍本”;论版本权威,当推“百衲本”。
二
张元济先生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印造居功甚伟。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98年因参与戊戌维新运动而被革职,以后去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年投资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后任董事长。建国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六世祖张宗松以涉园藏书闻名,至清道光年间,藏书因战乱散佚。张元济自青年时代即立“继承先世遗业之志”。经多年寻访,共搜集到原涉园藏书和刻书104种。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时,多方寻访,收购大批古籍,建立了藏书室,1908年命名为涵芬楼,1926年又扩建为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乃专门作为善本书库。张元济精于目录、版本和校勘之学,出版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编有书目《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张元济民国之初发愿“重校正史”,汇集善本,重新校勘、辑印古本全史,以恢复中华正史原貌。他在涵芬楼附近设立编校中心,广泛搜求各史善本,字字精校,页页修润。单是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校勘记》就达百余册。他亲自挑选纸张、监督印刷,克服了社会动荡、战火纷飞、原本校样屡遭焚毁等困难,历时18个春秋,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辑出版。其工程宏大,堪称“前无古人,泽被后世”。《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选版本,有宋刻善本15种、元刻善本6种、明清初刻3种。如《史记》选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选用宋景祐刻本;《晋书》则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用的是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所辑版本;《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193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发布了一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古籍校印流程,并刊出了“底样”与“清样”以作比较。
影印古籍时,如果所用底本不是初印,而是经多次刷印,字迹笔划难免模糊或断缺。如果找不到更清晰的初印本,就必须在影印过程中进行描润。所谓描润,即根据别的版本把模糊断缺描清、补足。根据《描润始末记》介绍,“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选底本最模糊的是宋刻南北七史,校勘工作十分繁难。其描润之法如下
原书摄影成,先印底样,畀校者校版心卷第叶号,有原书,以原书,不可得,则以别本,对校毕,有阙或颠倒,咸正之。卷叶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笔洁其版,不许侵及文字。既洁,覆校,粉笔侵及文字者,记之,畀精修者纠正。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笔。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弥补以硃笔。仍不许动易文字,有疑,阙之,各疏于左右栏外。精修毕,校者覆校之,有过或不及,复畀精修者损益之。再覆校,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监本、汲古阁本与精修之叶对读,凡原阙或近磨灭之字,精修时未下笔者,或彼此形似疑误者,列为举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见,畀总校。总校以最初未修之叶及各本与现修之叶互校,复取昔人校本史之书更勘之。既定为某字,其形似之误实为印墨渐染所致或仅属点画之讹者,是正之,否则仍其旧。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栏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畀精修者摹写,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总校覆校之。于是描润之事毕,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修既,制版。制版清样成,再精校。有误,仍记所疑,畀总校。总校覆勘之,如上例。精校少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为完善可印,总校于每叶署名,记年月日,送工厂付印。
“百衲本”以其对古代版刻的“妙手回春”之术,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描的一笔。独立成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与《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一起,也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三
鲁迅民国初年刚到北京时,对张元济印象不佳。
1912年9月8日,鲁迅在留黎厂直隶官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32册。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翻阅,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犹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入商务印书馆者矣。”他对商务印书馆在编辑过程中任意变乱名目表示了不满。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好在,张元济等编辑《四部丛刊》、《二十四史》是影印,而非标点。
随着时日推移,鲁迅对商务印书馆在古籍版本选择方面的精审和取得的业绩逐渐认可。鲁迅青年时代时排满思想很强,又经历过反清革命运动,故对清代纂修古书一直持批判态度。他的批评火力集中在所谓“钦定”《四库全书》上,因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清朝皇帝利用编纂图书进行民族奴役的“成绩”。他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说: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 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联系当前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鲁迅对清朝的文化统治就更痛恨,也更警惕,批判也就更严厉。事实上,鲁迅与《四库全书》还颇有些缘分。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图书馆工作,筹建京师图书馆之初,教育部决定调来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充馆藏,鲁迅被派前往接洽。不料图书半路上被内务部截收。后经交涉,《四库全书》终于归还了京师图书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的标志性藏书。
鲁迅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赞同张元济对古刻的精审选择。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正是纠正《四库全书》篡改旧文并恢复古书原貌的举措。鲁迅在《病后杂谈》中写道:
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
鲁迅购买这些古籍,是为了文化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参考。例如写完《病后杂谈》后,他收到预订的《四部丛刊》续编,立即从中摘取资料,佐证自己的观点。“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病后杂谈之余》)
但世人并不都像鲁迅这样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四库全书》因是“钦定”,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正如鲁迅说的:“‘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四库全书珍本》)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刊本,引来不同意见。蔡元培主张采用旧刻或旧抄本,以代替经全书馆馆臣窜改过的库本,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和学术界的陈垣、刘复等赞同蔡元培的主张。但教育部当局坚持原议,结果商务印书馆从命,于1934年至1935年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书231种。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一文中批评道;“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商务印书馆在版本选择上精益求精。在《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的扉页上,刊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的启事:“殿本《旧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并非薛氏原书,然不敢谓原书必亡也。昔闻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见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有谢在杭、许芳城藏印,甚以当时修史诸臣未见其书为惜。又明末福建连江陈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黄氏二老阁均有其书,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间。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虽选大典有注本,然欲餍读者之望,愿出重价,蒐访原书,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旧刻薛氏五代史原书者,倘蒙慨允见让,全书固极欢迎,即零卷散叶,亦甚快睹。……”
所以,当鲁迅在两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之间选择时,倾向性就不言而喻了。
鲁迅起意购买《二十四史》约在1929年。据日记记载,12月26日,“寄中华书局信,索《二十四史》样本。”但他最终选择了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原因大致有两个:一,百衲本汇集现存最好的未经篡改的古刻,质量让他放心。二,他的弟弟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一方面了解图书出版内情,一方面也可代他订购、取书,省却他不少精力。
于是,鲁迅于1930年8月26日“下午托三弟在商务印书馆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八月三十日影宋本汉书三十二本预付讫)。”1931年8月31日“下午得商务印书馆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期书《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记》、《辽史》、《金史》五种共一百二十二本。”1934年1月9日,“晚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取得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书》、《南齐书》、《陈书》、《梁书》各一部共七十二本。”1935年12月30日“往商务印书馆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种共一百三十二本,又《四部丛刊》三编八种共一百五十本。”
鲁迅不但购买了《二十四史》,还陆续购齐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1927年在广州时,他就看中了《四部丛刊》,如4月26日:“往商务印书馆买单行本《四部丛刊》八种十一本,二元九角。”这八种单行本即《韩诗外传》、《大戴礼记》、《释名》、《邓析子》、《慎子》、《尹文子》、《谢宣城诗集》、《元次山文集》。同时他也很注意史部的购买,如6月9日:“托广平往广雅图书局买书十种共三十七本,泉十四元四角。”这十种书是《补诸史艺文志》四种、《三国志裴注述》、《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六国春秋辑补》、《广东新语》、《艺谈录》、《花甲闲谈》。7月1日:“上午托广平买《史通通释》一部六本,泉三元。”到了上海,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他下决心购齐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许广平在《鲁迅与家庭生活》一文中写道:“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他绝不过问,然而他的买书帐自己是记下来的,当他想要买《四部丛刊》之类做文学史的准备材料时,曾经为了要花去几百块钱而游移不定了好久,还是我劝了才决定买的。”
四
鲁迅生于官宦之家,自小养成读书习惯。对待史书,他既阅读正史,也看野史。两相比较,他对中国历史获得一些清醒的认识。他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他是看了野史才知道明代皇帝的残酷的: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床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
从此,鲁迅对所谓正史,尤其是钦定的史书产生了怀疑和反感的情绪,并发表了一些批判性议论。他创作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是受了中国史书的启发:“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五四”时代,因为提倡新文化,鲁迅注意从中国历史中发掘负面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否定性言论,如,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中说: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他还说过:“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很使土人高兴;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热风•随感录 四十二》)更说到决绝处,他将中国历史简单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而在小说中,竟愤激地让狂人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两个字:“吃人!”
这个时期,鲁迅的文字给人们的印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全盘否定,例如“不读中国书”之类过头话,当时和后来颇遭诟病。然而,他自己却觉得这话不得不说,而且也不得不这么决绝地说,因为亡国就在眼前,只有发表此种“危言”,才会引动国人注意。今天的读者应该设身处地想想那一代人的内心焦虑,虽然这可能不大容易。
鲁迅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摆脱历史轮回,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人们一向夸大了鲁迅对野史的偏重。由于鲁迅对正史说过一些批评的话,人们就认为鲁迅完全否定正史。鲁迅对官修史书的确有严厉的批评,如说:“‘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重视野史也是实情:“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不满于正史的是其摆架子的态度和涂饰太厚的描述,而从他的读书经历看,他并不一味贬斥正史。正确的方法,是将正史和野史对照了看。拆除架子,去掉涂饰,就能看到真实,甚至能看到“民族的脊梁”。《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有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这段话堪称鲁迅的“晚年定论”。评价鲁迅,应该看前后的变化,应该看全面,而不能只强调他的“吃人”、“不读中国书”之类愤激之言。鲁迅及同时代人对中国历史形成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治学特点和思想方法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疑”——请注意,是“疑”而非全盘否定。“疑”也要有理性,要把握好分寸。鲁迅曾批评过有些学者过分“疑”,例如“古史辨”派某位学者“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当鲁迅静下心来,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全盘否定的话就少得多甚至几乎没有了。
鲁迅一生没有间断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校勘了很多古书。特别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对历史书又有了更多的中肯评价,显示了他的卓识。即便在写着《灯下漫笔》这类言辞激烈的文章的同时,他也在购读古籍。晚年,鲁迅开始实施自己心中蕴蓄已久的计划,撰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因为上海的图书条件不如北京,他甚至一度萌生了迁回北京的想法,后来因故未能实现。他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购置中国古代典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
鲁迅与同行讨论学术问题、向后生推荐图书时,也往往涉及此类古籍。如1929年初,他的学生和朋友章廷谦想购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的大举,则《史》,《汉》,《三国》;《蔡中郎集》,嵇,阮,二陆机云,陶潜,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也。”又如,他开给好友的儿子的书单中,提到《唐诗纪事》,就建议用《四部丛刊》本;而且还郑重地推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很显然,当进行学术研究时,他对《四库全书》也持有客观的态度了:这是一种便利和精到的工具书,可以合理使用。
1932年8月15日,鲁迅写信给台静农,说明自己的治学方法与胡适的治学方法的不同,指出,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在表达学术自信的同时,对《百衲本二十四史》因战火而延迟出版表示了遗憾,言下似有“等不及”的感慨和忧虑。
五
“百衲本”《二十四史》因其极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版本价值,从发行之初,即获各界赞誉。蔡元培赞扬张元济“博观精勤之成绩,所以嘉惠学子益无限量。”胡适写信给张元济道:“今早细看,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功劳最勤,功用最大,……”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盛赞:“《百衲本二十四史》所采获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定论者多千古未发之覆。”著名学者顾起潜的评论是:“煌煌巨编,非有高深的学养,难能做出宏大的规划;博访古本、善本,非熟悉中外藏书情况,难以集事;搜罗异书,发扬特点,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克有所发明。”该书风行七、八十年,至今为人称道,良有以也。
限于条件,《百衲本二十四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印数量无多,历经战乱、天灾,如今幸存下来的为数更少。鲁迅藏书中的这一套,得国家之力,现完整保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