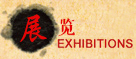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陈翔
1918年8月,营建两年的北大预科学生宿舍大楼在沙滩汉花园落成。因大楼用红砖砌成,人们形象的称之为“红楼”,其实际功能由原先的学生预科宿舍,改为北大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在红楼二层办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组织了北大图书馆的搬迁,他的办公室位于红楼一层的东南角。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年代,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南陈北李”同在一座楼里共事;马克思主义此时已开始在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楼里传播;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成长。这一切都预示着,北大红楼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研读日本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并有意识的研究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并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以一个进步历史家的眼光,第一个把十月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做了比较。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天安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相继举行演讲活动。李大钊在他的《庶民的胜利》讲演中,揭示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2]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深刻根源是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是在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根本原理。他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反映了李大钊的无产阶级倾向和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力。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撰写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明确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豪情的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
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1918年12月,李大钊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而这里又作为这一刊物的编辑所。《每周评论》为李大钊开辟了一个更加有效快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9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纪元》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称之“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他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悟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4]
李大钊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于他平素谦虚和蔼,待人诚恳,又有阅读新书的方便条件,当时北大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图书馆主任室分内外两间,外间作会议室,内间作办公室,两间不大的屋子还有个“饱无堂”的雅号,因为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5]。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不仅是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也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不少进步学生常来请李大钊介绍、推荐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和在后来出版的《新青年》6卷6号上,连载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
《新青年》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汇集了多篇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除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有顾照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6]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这些人无论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四面出击。陈独秀此时因散发传单而被关押在警察厅,继续着“以图根本之改造”的抗争;胡适一面大谈“实验主义”[7],一面继续倡导文学革命,宣传“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8];唐俟(鲁迅)告诫人们“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9]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并针对腐败时政,发表大量的随感录;吴虞无情地抨击“吃人的礼教”[10],延续着伦理革命的宗旨;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刘半农等则不间断地写着白话诗。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开始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而李大钊则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0年,李大钊受聘为北大教授后,率先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在现存档案中,有北大学生贺廷珊“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答卷。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李大钊给这份答卷打了95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大钊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情况。
1920年起,中国发生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李大钊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室,组织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参加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即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教室挤不下,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正反两方辩论结束后,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声音不大,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使人心悦诚服。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的发言引起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1]
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
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促使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盛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流派之一,也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早在1918年冬,李大钊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西方人口论学家马尔萨斯的音译极为相似,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时学说研究会”,以防在必要时对警察方面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12]北大学生中一些先进分子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一些不懂或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好奇的人,开始也被吸引加入了。研究会第一次聚会在李大钊办公室内举行。虽然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工作,也没有更多的青年参加,但是,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还是出现了最初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一年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五四前夕,同在北大红楼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一时期,他开始从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和法国民主制度,转向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表明他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初,陈独秀正是带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念离开北京,辗转前往上海,在那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基地。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这里曾举办座谈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并几次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13]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其成员发展很快。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介绍,先认识了李大钊。两人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后,李大钊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根据罗章龙回忆,他们的会面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还谈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为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使中国学生感到耳目一新,使他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14]
由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即将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前,李大钊、罗章龙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再次在图书馆主任室召开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李大钊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他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并在1920年8月,主持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在这里又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随后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拥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十几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需要强调的是,五四运动期间,身居红楼的“南陈北李”,其精神领袖地位唤起更多先进青年树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17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人物相继聚集北大。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的“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建筑;陈独秀的威望更是与日俱增,他在进步青年心目中,是足以起到他人所不能有的呼风唤雨的作用的。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的影响力远大于李大钊;但在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来说,更能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两位进步思想界的明星逐渐引领青年中的崇拜者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当1920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生长起来。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三、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成长的摇篮
从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批进步学生的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变。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开始大量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
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一个重要社团,邓中夏为该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社团成立之初,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开展平民教育活动。讲演团最初活动局限于城内,在街头或利用一些有庙会的寺院作不定期讲演,以后则利用官立的讲演所并在北大旁边设点定期讲演,讲演的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大体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等,依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1920年起,为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悟,积聚工人阶级力量,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邓中夏等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到长辛店与几个工人接头,并在次年1月,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开办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这所学校表面上以补习为名,实际是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这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最早的工人阶级的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通过组织工人学习文化与政治,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取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中的著名人物,五四运动中,他因爱国活动曾遭到军警的逮捕,也曾代表北大学生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五四运动后,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书籍,通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15]1920年初,当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建党之际,张国焘辗转上海、北京之间,成为“南陈北李”的重要联络人。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在北大会谈后,常常和张国焘谈论马克思主义,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李大钊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曾希望少年中国学会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张国焘赞成这个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共同策划,从而成立了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7月,张国焘去上海。行前,李大钊委托他向在上海的陈独秀转达自己的意见,大意是,他虽然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独秀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16]张国焘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2号见到陈独秀后,转达了李大钊的意见。陈独秀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17]此后,这个主张成为张国焘与陈独秀多次谈话的内容;同时还涉及到共产党的党纲政纲、党章和实际组织等问题。8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向李大钊转达了和陈独秀的一系列谈话和意见,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8]随后,他们多次与陈独秀通信,开始了建党工作的具体商讨。
随着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1920年11月,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随之组织起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几乎又都是青年团团员。高君宇当选为第一任书记。青年团以北大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初期工作主要是在各个学校联络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相机发展团员,并组织一部分青年赴苏联参观学习。1921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原来所设的四部制及委员制改为执行委员会,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分别当选为书记、组织委员、会计委员,李大钊当选为出版委员。4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团执行委员会在北大红楼举行会议,讨论“五一”举行游行、刊行一至二种宣传小册子、团员在运动中的分工、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及平民教育讲演所的情况以便进行社会主义的指导、如何组织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以及筹备“五一”节讲演会及如何研究主义等等问题。后来又在北大二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成立由高君宇、罗章龙、王复生等7人组成的“五一运动委员会”,制定“五一”节所要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还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壮大输入了新生力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决定从秘密走向公开,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作为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之一,罗章龙找到蔡元培,希望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一个启示,他向蔡元培陈述:“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运用,均有超越前人之处,我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是试图对于革新思想界,做些促进工作。”他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马克思学说今后对中国人行将发生不可估计和极深远的影响。”[19]罗章龙一席话打动了蔡元培。1921年11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公开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研究会成立了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其中除专门研究马克思学说外,还研究当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各派社会主义,并就有关问题组织讨论会。此外还配合研究工作组织定期讲演会,李大钊等都为该会做过专题报告。为了有助于研究,该会还集资成立了专门的图书馆——“亢慕义斋”,收集有关研究的汉、英、俄、德等各种文字的书报杂志数百种之多。 《北京大学日刊》不定期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消息,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在刊登的《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上,注明发起人为19人;到了1922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宣称研究会会员已增至63人。罗章龙成为研究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1922年统计的研究会100多名会员的名单中,就有25名工人,他们主要来自于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铁路段,其中有邓培、王荷波等著名工人领袖。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大都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等。当时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公推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组织内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负责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团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
综上所述,从北大红楼建成之日起,由于李大钊的作用,无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思想基础方面,还是在发展和健全组织以及培养、准备干部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红楼也经历了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后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与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南北呼应。主要由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组织的最早基础。它是当时几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重要的小组之一,其地位和作用,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相比,是不相上下的。正因如此,北大红楼在1961年即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赋予这座红色建筑以新的含义,人们也从这座建筑中,隐约看到中国共产党从90年前呱呱坠地的艰辛走向今日的辉煌。
--------------------------------------------------------------------------------
[1] 《言治》1918年7月1日第3册
[2] 《新青年》5卷5号
[3] 《新青年》5卷5号
[4]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5]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6] 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为“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根据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石川祯浩考证,“渊泉”应是《晨报》总编陈溥贤的笔名。这一说法,得到中国学术界不少学者的认同。
[7] 《新青年》6卷4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
[8] 《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
[9] 《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
[10] 《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
[11]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295-296页
[12]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293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8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1月
[14]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9月第一版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8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1月
[1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86-8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1月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92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104页
[19] 罗章龙:《椿园载记》58页,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9月第一版
 0
+1
0
+1